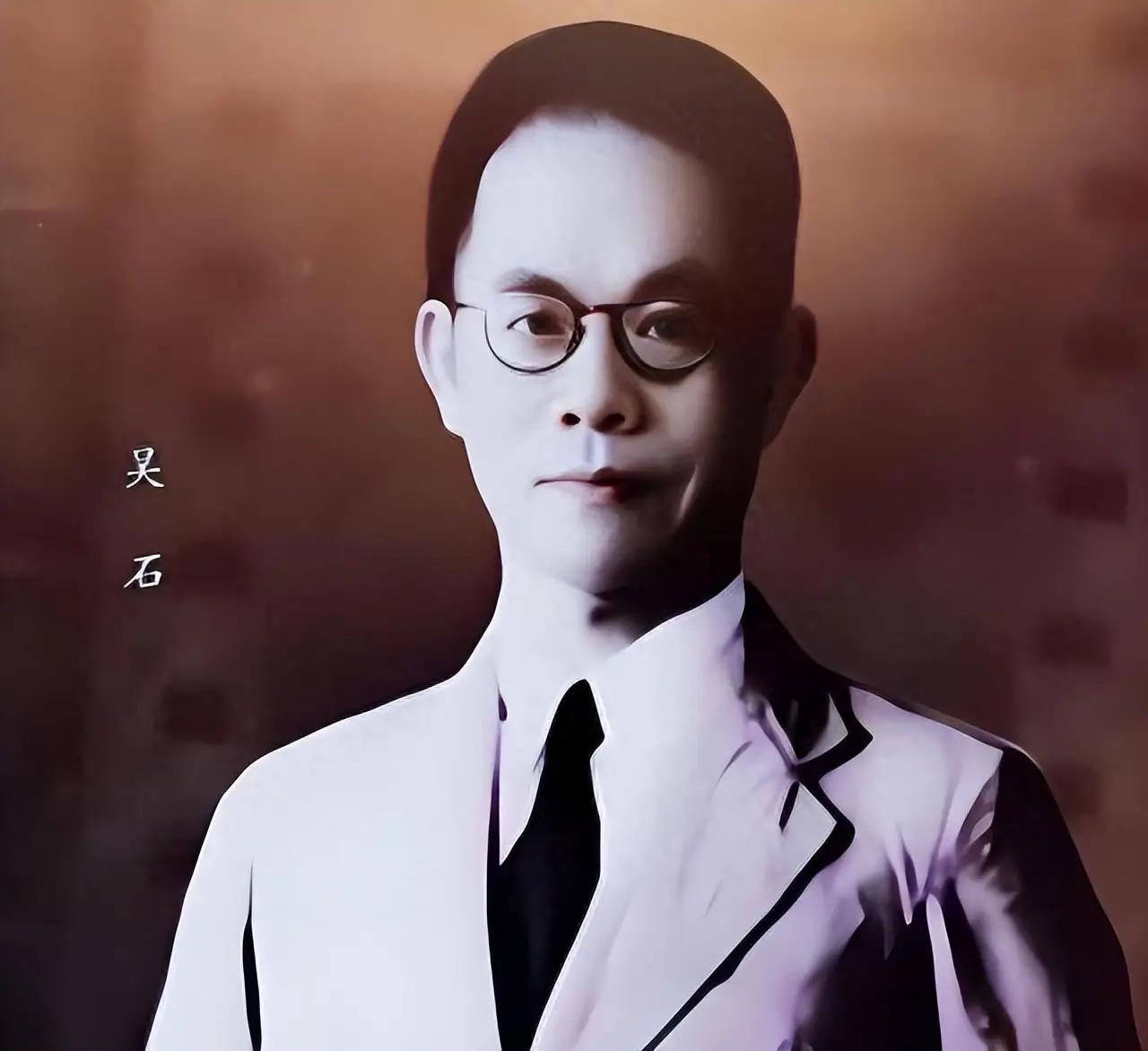2012年,蒋英在北京逝世,葬礼十分隆重,她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可是,却有人却认为蒋英得到高规格的待遇,是因为科学家丈夫钱学森。 这话要是让蒋英自己听见了,估计得叹口气。 确实,很多人一提起蒋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钱学森的夫人”。可懂行的人都知道,她可不是那种躲在丈夫光环下的人——单说“蒋英”这两个字,在新中国声乐界,本身就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她的底气,打小就扎了根。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军事理论家,被称为“中国近代兵学泰斗”,可家里从不缺艺术氛围。母亲是大家闺秀,弹得一手好钢琴,哥哥姐姐们要么爱画画,要么迷戏曲。蒋英六岁就跟着母亲摸琴键,十岁被送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那会儿她就能站在礼堂里唱《茶花女》选段,声音清亮得像初春的泉水,连校长都夸“这孩子天生吃声乐这碗饭”。 1937年,17岁的蒋英跟着父亲去了欧洲,一脚踏进了音乐的殿堂。在德国柏林音乐学院,她师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克兰德尔,每天天不亮就去琴房练声,连吃饭都在背歌词。有次练《蝴蝶夫人》里的咏叹调,一个高音总唱不稳,她硬是对着镜子练了三个小时,直到嗓子发哑才罢休。后来转到瑞士苏黎世音乐学院,她又主攻歌剧表演,把意大利语、法语的发音抠到极致,老师说“蒋英对音乐的较真,比德国人还刻板”。 1947年回国时,蒋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女高音歌唱家。她没借着父亲的名气找轻松差事,反而一头扎进了刚刚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成了声乐系的第一批老师。那时候条件苦,琴房不够用,她就带着学生在走廊里练声;教材稀缺,她连夜手写乐谱,把自己在欧洲学的技巧一点点拆给学生。有个学生记得,蒋老师上课从不让人“只练技巧不练情”,教《黄河大合唱》时,她会先给学生讲抗日战争的故事,直到学生眼里有了光,才让开口唱——“声音里没感情,再高的音也没灵魂”,这话她跟学生说过无数次。 钱学森回国后,两人的家成了音乐与科学的“交汇点”。钱学森总说,蒋英的音乐是他科研之余的“解压药”,有时候对着复杂的公式头疼,听蒋英弹一段巴赫,思路突然就通了。可蒋英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这些,她照样每天去学校上课,周末去剧院演出,连钱学森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天,她还是按原计划给学生上了两节声乐课。有人劝她“现在可以歇一歇,享享清福了”,她却摇头:“我是老师,学生还等着我呢。” 她教出的学生里,出了不少响当当的名字——比如歌唱家李双江、梦鸽,还有声乐教育家金铁霖,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声乐界的中坚力量。直到80多岁,蒋英还在给研究生上课,耳朵照样尖,哪个学生的气息没沉下去,哪个字的发音没到位,她一耳朵就能听出来,一点都不含糊。 那些说她“靠钱学森”的人,大概没见过她站在舞台上的样子——聚光灯下,她穿着素雅的旗袍,一开口就能把整个剧场的人都“攥”住;也没见过她在课堂上的认真,握着学生的手教气息控制,额头上渗着细汗,眼里全是对音乐的热爱。她得到的尊重,从来不是因为“钱学森夫人”这个身份,而是因为她用一辈子的时间,把西方歌剧的精髓带回中国,把中国民歌的韵味融入声乐教学,硬生生在新中国的声乐史上,刻下了属于“蒋英”的名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