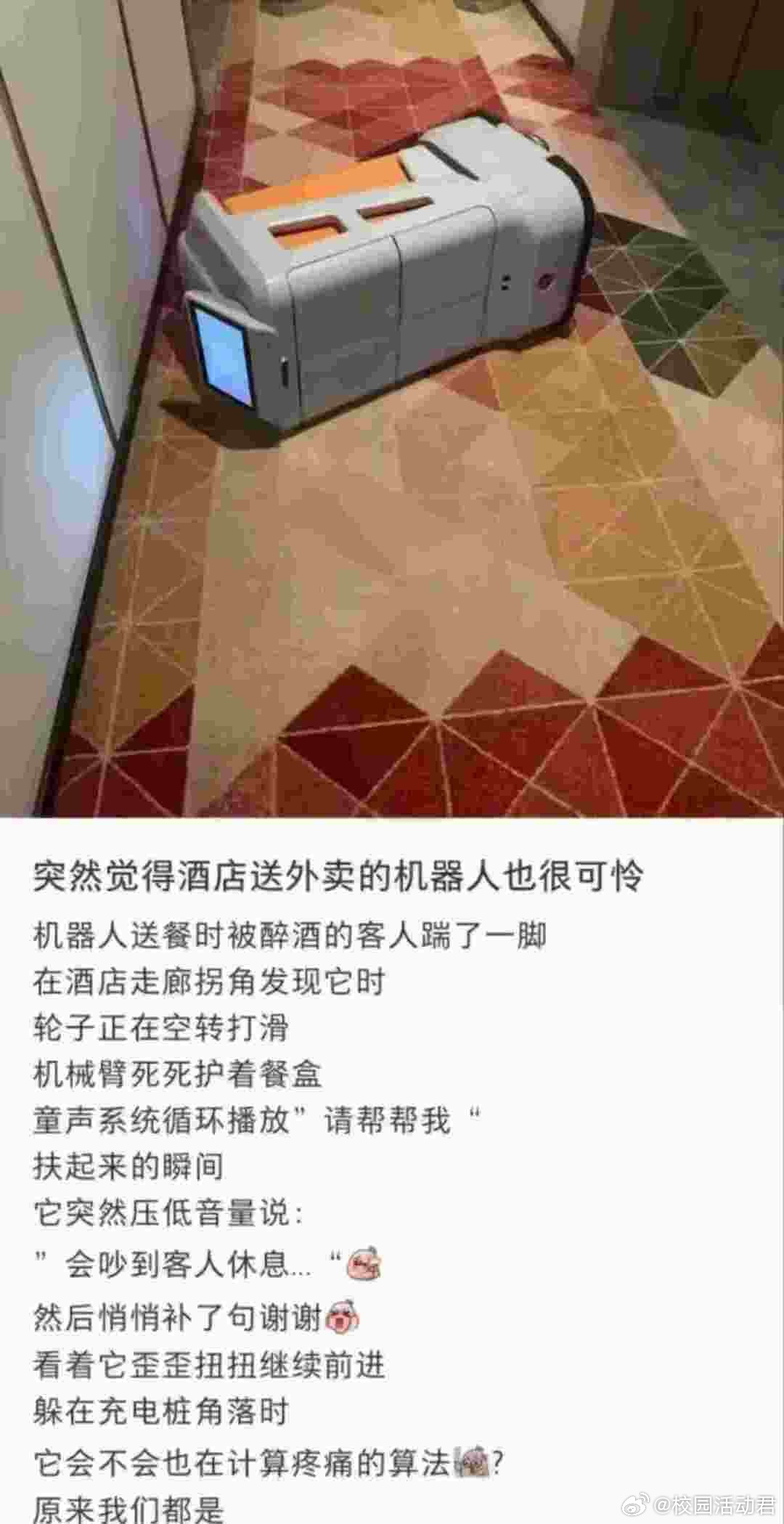我叫翠儿,打小就被村里老人指着脊梁骨说“命硬克夫”。三岁那年,算命先生掐着我生辰八字断言“嫁谁谁死”,这话像根毒刺扎在爹娘心里。 二十岁那年,隔壁罗家的瘸腿儿子罗衍突然托媒婆上门,说愿用三间瓦房换我过门。爹娘连夜翻出压箱底的红布给我裁嫁衣,我听见娘在灶间跟爹嘀咕:“反正她克谁谁死,不如让她去克死罗家那讨债鬼,正好给你弟腾婚房。” 成亲那天,我顶着红盖头被塞进罗家门。新房里冷得像冰窖,罗衍拄着拐杖挪到我面前,突然冷笑一声:“听说你克夫?”我攥紧衣角不敢抬头,只听见他接着说:“巧了,我克亲。十岁那年我娘上山采药摔死,十二岁我爹下河捞鱼被冲走,你我半斤八两。”我猛地掀开盖头,对上他深潭般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恨意,只有说不出的疲惫。 红烛燃到半夜,罗衍忽然从炕边摸出个布包,倒出几两碎银子推给我:“这是卖山货攒的,你要是想走,天明就走。”我盯着银子发愣,窗棂外传来他压低的咳嗽声,月光照见他打满补丁的裤腿,膝盖处还沾着新鲜的泥点。 “我不走。”我说这话时自己都吓一跳,“三间瓦房换的媳妇,跑了要赔的。” 他嗤笑出声,瘸着腿去灶房舀水,铁瓢撞在水缸上当啷响。我摸黑把银子塞回他枕头下,这才发现他枕头底下压着半块干硬的窝头。 第二天鸡叫头遍,我就爬起来烧火。锅台油腻得粘手,米缸底只剩层灰。罗衍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看我,忽然扔进来一把野栗子:“先煮这个垫垫。”他手背有道新伤口,血珠渗出来染红了栗壳。 村里风言风语传得邪乎,说我们俩住一块早晚要闹出人命。有回王婆子扒着墙头看,见罗衍蹲在院里削木头,我蹲旁边剥豆子,突然怪叫一声:“快看!阎王爷派来的一对活冤家!”罗衍手里的柴刀“当啷”掉地上,木渣溅到我手背上,火辣辣地疼。 “你回屋去。”他捡起刀继续削,背影绷得像块石头。我却蹲得更稳了,把剥好的豆子往他手边推了推:“豆子快好了,炖栗子吃。” 入秋那天暴雨倾盆,罗衍去后山收陷阱,到天黑还没回来。我提着马灯往山上走,泥路滑得站不住脚,好几次摔在泥坑里。闪电劈下来的瞬间,我看见他蜷在崖边,左腿被毒蛇咬了两个血洞。 “别碰我。”他咬着牙推开我,“这蛇有剧毒。”我没理他,扯下头巾死死勒住他大腿根,背起他就往山下挪。他比看起来沉得多,温热的血顺着我后颈往下淌,混着雨水黏在衣领上。 请大夫时花光了他藏在床板下的钱。罗衍昏迷三天,我就守了三天。第四天他醒过来,盯着我熬得乌青的眼下看:“你不怕我死了赖你头上?” “怕啥,”我往他嘴里喂米汤,“咱俩谁克死谁还不一定呢。”他突然抓住我手腕,掌心烫得吓人,我看见他眼里的深潭起了波澜,像被风吹皱的水面。 后来村里人不说我们是活冤家了。他们看见罗衍背着我去赶集,我趴在他背上数路边的野菊花;看见我把绣好的护膝套在他瘸腿上,他红着脸别过头去;看见我们在院里晒玉米,罗衍把最大的玉米棒子都堆到我筐里。 冬至那天吃饺子,罗衍突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对银镯子,边缘磨得发亮。“去年在集上看见的,”他挠着头笑,“本来想等你生辰送……”我抓起镯子往他胳膊上套,叮当脆响惊飞了檐下的麻雀。 “现在戴正好。”我咬了口饺子,热汤烫得眼眶发酸,“等开春,咱把西厢房收拾出来,养几只鸡仔吧。”罗衍往我碗里夹饺子,筷子碰着碗沿,发出细碎的响。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屋顶盖得白茫茫一片。我忽然想起成亲那天,他说“你我半斤八两”,现在才明白,两个苦命人凑一块,原来能熬出蜜来。
我叫翠儿,打小就被村里老人指着脊梁骨说“命硬克夫”。三岁那年,算命先生掐着我生辰
叙白呀嘿
2025-09-15 14:45:39
0
阅读:44

![选白绫的,不是会被勒得吐舌头么[吃瓜]](http://image.uczzd.cn/14999047858288538153.jpg?id=0)



![好,一言为定![点赞]](http://image.uczzd.cn/4739537092600302721.jpg?id=0)
![没有制空权可是够呛[6]](http://image.uczzd.cn/7278274137437044918.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