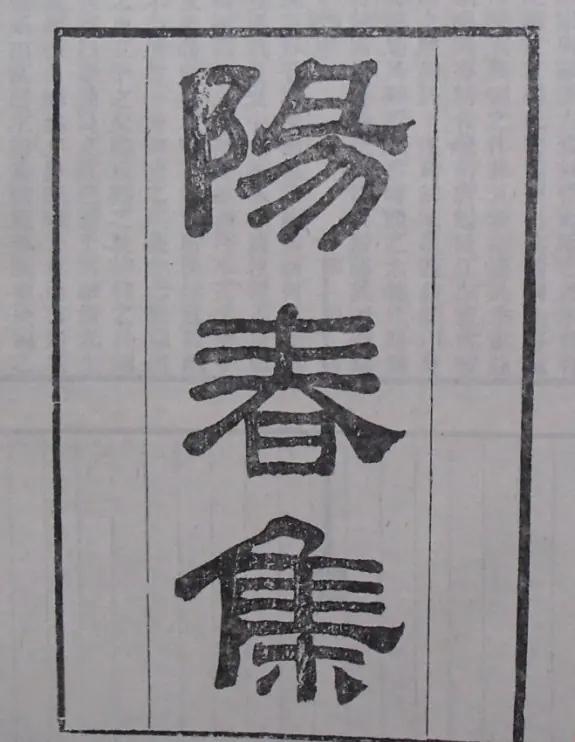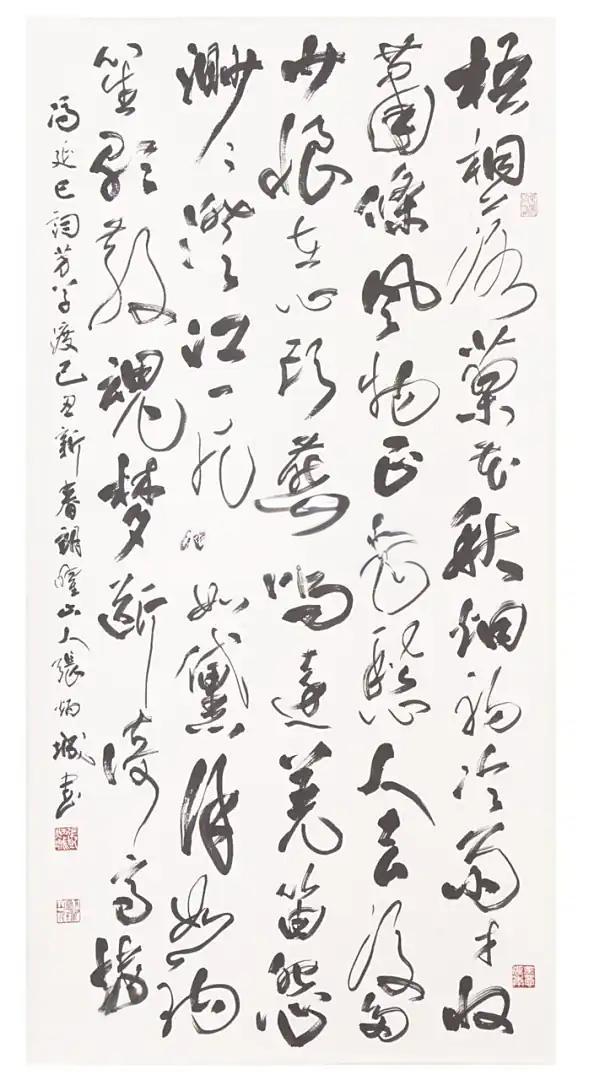张若虚的作品只有两篇传世,却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力压一众唐代诗人。冯延巳则作品数量颇丰,有《阳春集》流传,他的创作开了北宋词体风气之先。这两位作家一位生长于初、盛唐之交,一位活跃于五代南唐文坛,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相去甚远,两人作品的思想与特点却有相似之处。 《春江花月夜》原为宫体,自然离不开离人思妇,但诗人在传统的相思别离中,感受到自然万物年复一年伫立在天地间,只有人是宇宙的过客,相较于宇宙的浩大和人世的长宏,人的思考都显得渺小了。 这种超越时空的认知充斥着无可奈何的感伤。诗人在春水旁月夜下,感受到江山明月的永存,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有限,这样两相对照就生发出无尽的惆怅意味,这是诗的第一层意味。 人生如寄,长江流水正如人世的更迭不停,只有明月永远高悬空中。然而明月虽照耀万物,此刻在空中是“孤”的,皎皎空中只有一轮孤月。 月的孤独不止此刻,它看遍了人世轮回,孤独即是它的生存。这是诗的又一层意味。人生虽短暂,但人在抬头望月的刹那,感受到的孤寂与空中的孤月是一样的,人与月,人与宇宙,瞬间与永恒,无常与有常在此刻合而为一,这是诗的第三层意味。 《春江花月夜》以夜里的离愁别绪为底,写春、江、花、月无不含情,在对情的描摹和探寻中逐渐深入,直至探寻到宇宙的奥秘,使个人的情感体验上升成为带有哲理意识:人生的无常和孤独的永存都是不可变更的规律。 这种情中有思的手法正与冯延巳不谋而合,冯的代表作《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便是典型代表。 《鹊踏枝》从闲情起笔,句句以景结情。这种闲情并非纯粹的闺情春愁,而是人生普遍的一种感受,“惆怅还依旧”又“何事年年有”都点出这是永恒存在的忧愁和惆怅,跟随春去秋来的年节,成为人生的一部分。为了摆脱这样的闲情,作者不辞常年病酒,然而仍旧无法抛去,更加深了惆怅带来的痛苦。 词中没有确指的人和事,是冯延巳的创作特点之一。冯延巳的人生经历颇为复杂,他能在乱世偏安一隅,但南唐的倾颓之势已无法逆转;身处宰相之位,却也几经宦海沉浮。 冯延巳爱写愁,他有许多欲说而不可言说的情感和思想,都倾洒到词中,他的词作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含蓄、不可直接言尽的意味。另有几首《鹊踏枝》如《梅落繁枝千万片》和《几日行云何处去》也都言及愁,却也不能在词中见到愁的缘由。 以《谁道闲情抛掷久》来看,整首词的意境跳出一般的相思别离,上升成为人类普遍的情感。人生不得完美,痛苦忧愁总要与人相生相随,这亦是宇宙间不可打破的规律。 词的最后作者荡开一笔,没有回答为何愁绪永在,转而描写一幅人在景中的画面,“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不再言情,但孤寂之感油然而生。在无奈的孤寂后,伴月而归就成了不可解之解,此刻桥头临风站立的人浑身披上一种跳出情结与愁绪的遗世独立之感。这与《春江花月夜》诗中最后两句“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有异曲同工之妙。 词境和诗境有异,两首作品在最后不约而同地走上同样的道路。个人的生命必将消亡,但生命的形式是永存的,人在生命更迭中走完自己的轨迹,或许是无奈的选择,也可以是大彻大悟后豁达的洒脱。这也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在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情感的共通体验总能超越时空、超越身世,无论古今中外。人生无常,但无常永恒,所以盛唐的明月照耀五代,亦拂及现在每个举头望月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