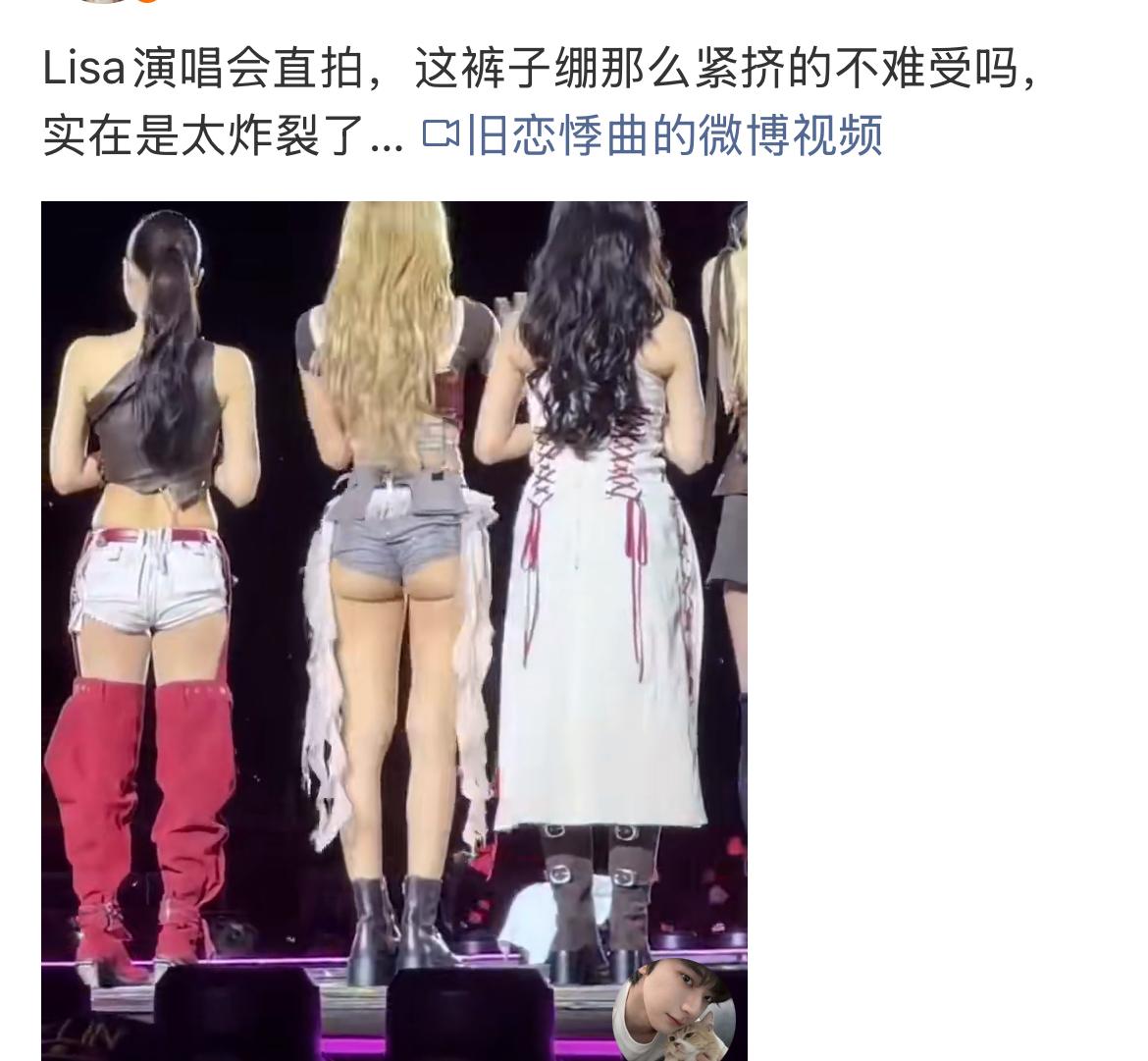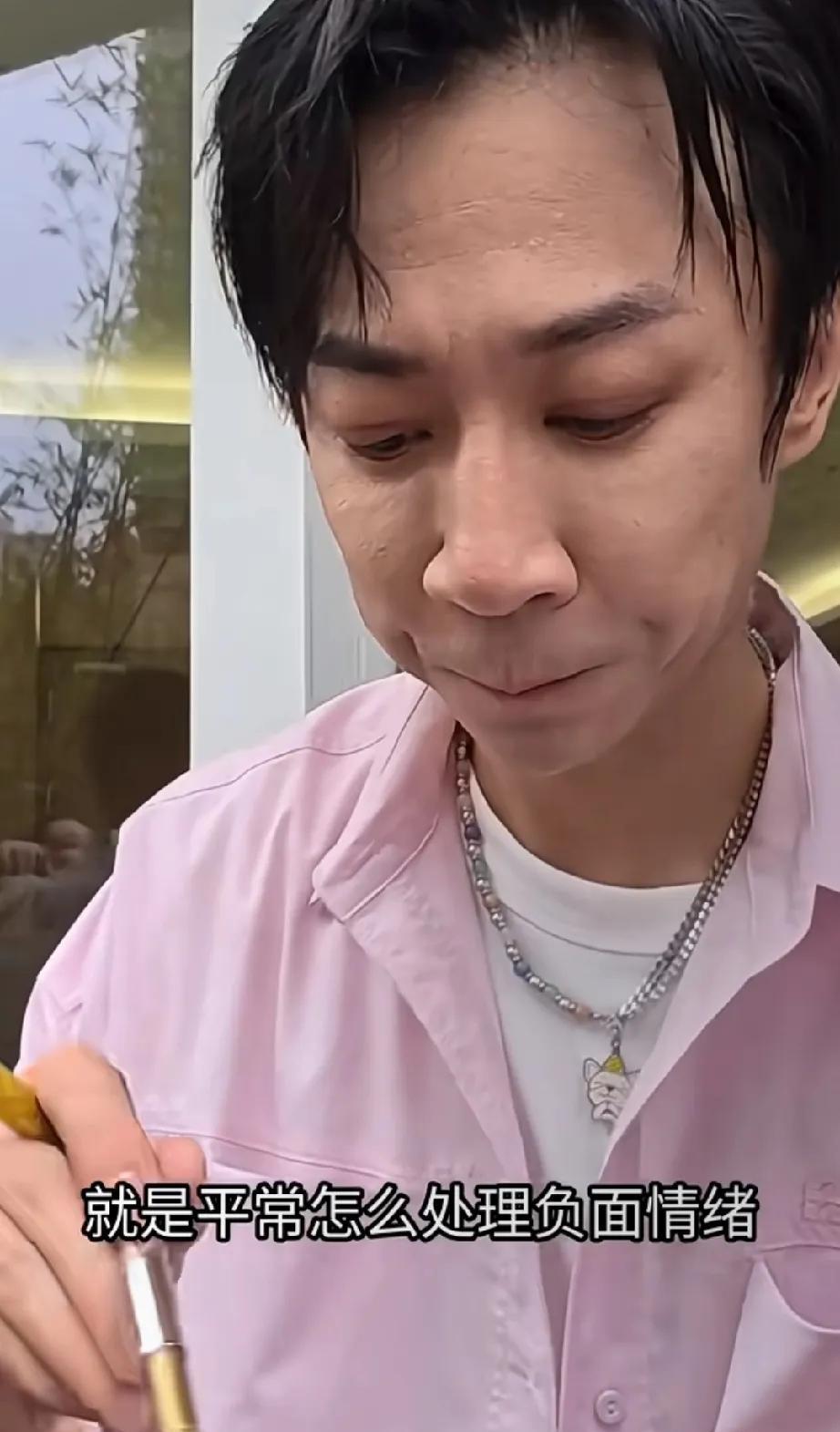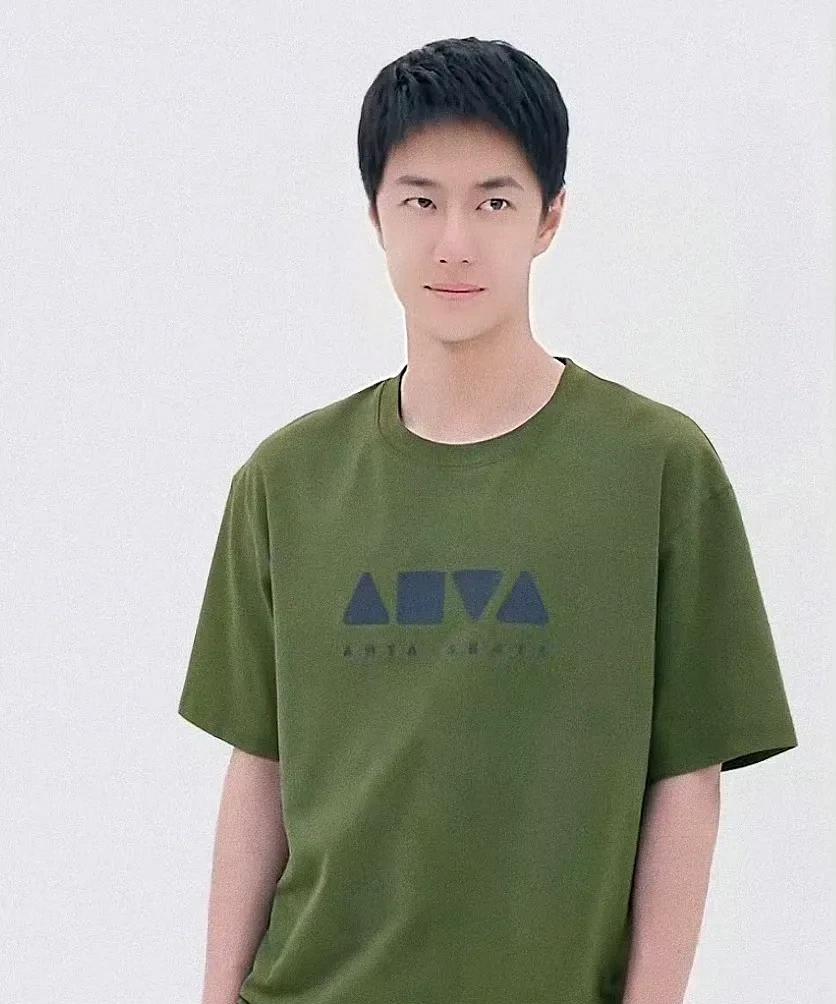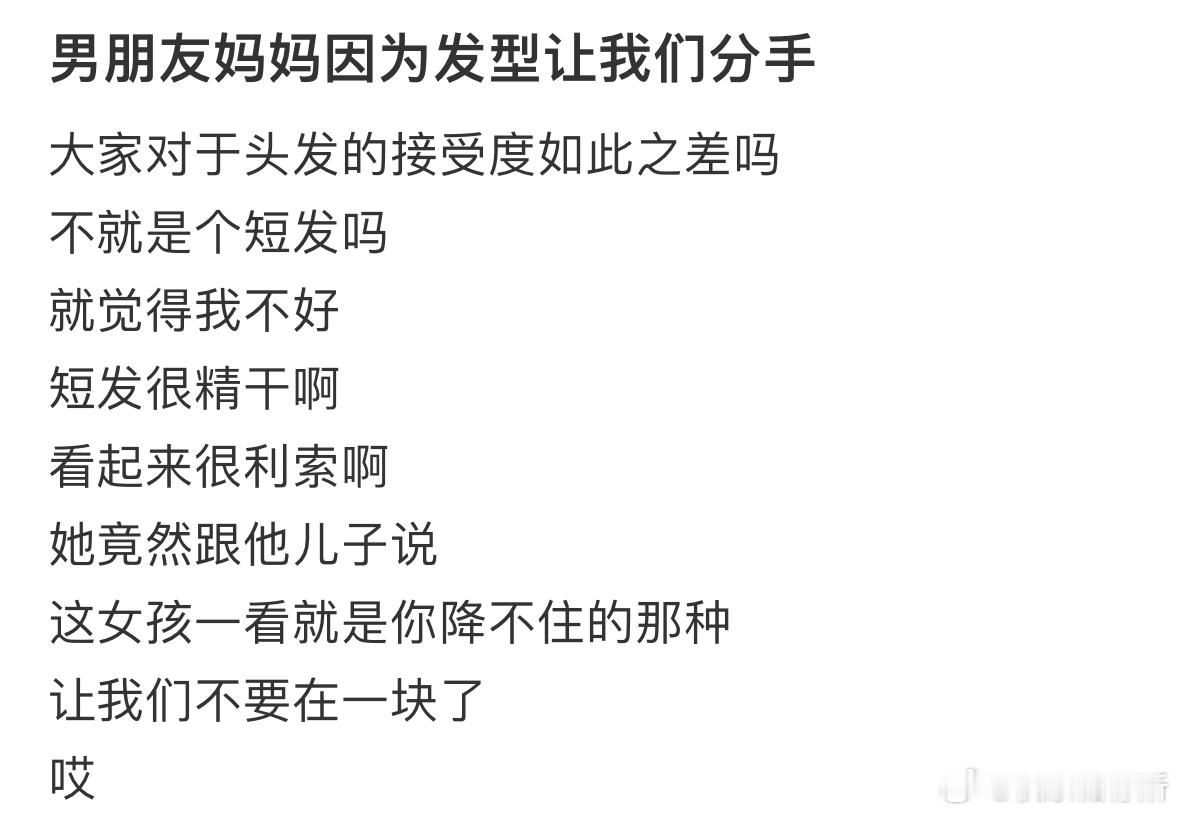1968年,张大千的四姨太徐雯波,正跪在地上拜师。她妆容精致,发型讲究,一身华丽的旗袍,勾勒出她娇好的身材。身上的珍珠项链和手镯首饰,让她显得尊贵又洋气,的确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人啊!
她是跪着的。 旗袍贴着膝盖,腰板挺直,珍珠挂在锁骨上,半点不晃,像是老照片里的人突然动了起来——不说话,眼睛亮着,一直望着面前那位书画老先生,叫马寿华。男人微驼着背,伸手扶她,身后一个熟悉的身影站着,手握着宣纸扇子,一言不发。张大千——就是那位被称作“大千居士”的张大千,此刻站在旁边,像是个局外人,也像是半个见证人。 那是1968年,台北。 照片传出来后,不少人先看的是她的脸。的确,是漂亮的。那种漂亮不张扬、不慌不忙,骨子里透着南方女人特有的细致和韧劲。可是照片没有声音,看不出她喊的是“老师”,还是“先生”,也没人知道她膝盖磕在地板上时有没有疼。这个动作很轻,但一旦定格,就像一场命运的回头。徐雯波,从此不仅是张大千的妻,也成了别人门下的弟子。 这事,要往回翻。 二十年前,成都的天是雾蒙蒙的。张家宅子里常有人进出,女儿请朋友来吃点心、听唱片,偶尔也让父亲看看她们画的梅花兰竹。那年张大千已经四十八岁了,鬓角添了几根白,却越发爱笑了,眼神还是那副戏谑中藏着打量的样子。徐雯波第一次来,穿着一身灰棉袄,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张大千递给她一盏热茶,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声音很轻,像哄猫。 谁都没想到,他日后竟向她求了婚。 她那年十六,脸上还长着没消的青春痘。张大千说:“你像小荷。”她听不懂,只低头。两人年纪差了整整三十岁,外头人看了,议论纷纷,说他老牛吃嫩草、说她图名图利。但家里人知道,她那阵子每天傍晚还是回去煮饭、洗碗,母亲念她要多读书,她只说:“大千说,让我看书。” 新婚那晚,她低声叫了句“伯伯”,他忙伸手捂她嘴,像是怕被谁听到似的:“叫我大千。” 这个男人,连自家姑娘的朋友都敢娶,心里怕是没什么不能破的规矩。 婚后的日子倒也平静。她穿着旗袍在院子里剪花枝,他坐在画案前调墨,有时也把她喊过来,让她帮忙晾画。她从没想过要学画,张大千也不逼她。家中大大小小的宴请,她学着做主妇,跟着长辈说话寒暄,遇着藏家来访,她便站一边,不多嘴。张大千倒也疼她,曾画过一件旗袍给自己女儿,那是后来拍出两百多万的《菡萏真丝旗袍》,上头的荷花一笔一笔勾着,是他心头难言的愧。 愧给谁?外头人猜是女儿——毕竟他娶了女儿的闺蜜。但更多的,也许是愧给这些年辗转陪着他东奔西走的女人们。 1949年冬,局势紧张。他们走得急,带不走几件东西。徐雯波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脚还没完全恢复。那天在新津机场,她穿的是一件绒布外套,张大千一手提着画轴,一手牵着她。他们去了香港,又去了印度,后来落脚巴西,再后,又搬去了美国加州。 在卡梅尔的那些年,海风常年吹得人骨头发酸。她守着屋子,一日三餐照料一家老小,外头人说她福气深厚,有张大千做丈夫,哪里知道她一个人在厨房灶台前烫了多少次手。张大千依旧活跃,画展一场接一场,宾客来来往往,她笑着应对,从不失礼。 她学会了不多问。哪怕他又结识了哪个舞女,或是哪位富太太。她知道,这样的男人不属于谁。 直到那天在台北。 她突然跪下了。不是为张大千,是为了另一个男人,马寿华。外头说他比张大千名气小,但规矩全、派头大,拜了他等于名正言顺地入了门。她头发盘得高高的,发簪是翡翠的,一动不动。张大千站在一边,看了半晌,也没说什么。 有人猜,他是默许;也有人说,他是把她“外包”出去,不想管。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能讲得清。只知道从那之后,徐雯波在一些场合开始被称为“马门弟子”。她挂的画,也开始署名。 不是大千夫人,而是“徐雯波”。 这些年,她也捐过不少东西。张大千去世后,她把印章、藏品整理出来,捐给博物馆。有些拍卖会上出现她名字的条目,那些人问,她是谁?她是张大千的哪一房?可她从不解释,也不争辩。她不画画,但看得懂每一笔;她不说话,却懂得什么时候退一步。 她的故事,从来没被大张旗鼓地写过。但她的身影,藏在每一幅画边的画案旁,藏在宴会间她递茶的手势里,藏在那场拜师礼上她跪下的动作里。 那动作很轻,像风吹开的纸门。膝盖落地,没有声响。 可你要是把那张老照片翻出来,仔细看,会发现她眼神里有光,像是知道自己这一跪,写下的,是自己一生中最响亮的一笔。她不问归属,不争头衔,只是在画家与世界之间,悄悄留下了一道她自己的身影。 拜师那天,天阴着,屋檐滴着水。她站起来时,裙摆沾了些灰,没人去拍。她抬头,微笑了一下,手里还攥着一方丝帕,指节泛白。张大千转过身,往门外走去,扇子没再合上。她没追,只是低头,把那根松掉的发簪重新插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