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将军,帅化民说,从小到大我一直很奇怪,我从哪里来,我上学时,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没有遇到过和我同姓的。 这种独特感随着年岁渐长,慢慢变成了对根源的探寻欲。 父亲告诉他,他们的根在大陆,帅姓在那边并不稀奇,家族祖上在江西奉新县有深厚的根基,只是因为历史变迁,一家人辗转到了台湾。 父亲还说起,当年每次回村,都会在村口下马步行,这是祖辈传下的规矩。 这些话像种子落在帅化民心里,让他对那个从未谋面的祖籍地生出无限向往。 1943年,帅化民出生在江西奉新,六岁时随家人从上海离开大陆。 儿时的记忆模糊又遥远,但父亲口中的家乡故事,还有那句“村口下马”的叮嘱,一直刻在他心里。 父亲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却总在饭桌上念叨老家的风土人情,讲给祖父修的那座墓。这些细碎的念想,成了帅化民心底对故土最原始的牵挂。 2009年,一个消息传来,祖父的墓碑在老家被找到了。 当时的帅化民已经年过花甲,听到消息的那一刻,积压了大半辈子的寻根念头突然喷涌而出。他立刻安排行程,踏上了回乡的路。 那是他第一次回到奉新县赤田镇店上帅家,宗亲们早已在村口等候,拉着他的手说起这些年帮着照看祖墓的事。 站在祖父墓前,听着乡音浓重的讲述,他突然懂了父亲为什么总念着回家,那是血脉里扯不断的牵绊。 也是这次回乡,他特意记住了“村口下马”的传统,说以后回来,一定要走着进村。 2017年,帅氏祠堂竣工,帅化民带着全家老小再回奉新。 祠堂里的族谱泛黄却清晰,一代代名字排下来,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海峡两岸的族人紧紧连在一起。 他跟着宗亲们祭祖,听老人讲家族迁徙的故事,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追跑,突然觉得,所谓的“家乡”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这些活生生的人,这些热气腾腾的烟火气。 那时候村子里多是土路,下雨就泥泞,但宗亲们的笑脸比阳光还暖。 再后来就是2024年初夏,八十多岁的帅化民第三次回乡。 车子快到村口时,他让司机停在路边,自己拄着拐杖慢慢往里走。 村口的老人们远远就迎上来,“化民回来啦”“身子骨还这么硬朗”,招呼声此起彼伏,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像欢迎久别归家的亲人。 有人拉他去家里坐,泡上新采的茶,端出刚蒸的米糕,说着这几年村里的变化,“你看那条路,去年修成柏油的了”“村东头盖了新楼房,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住了”。 他坐在宗亲家的堂屋里,听着乡邻们细数日子的改善,眼睛里亮闪闪的。 聊了许久,他坚持要自己走到祖父墓前,说“脚沾着地,才算是真的回来了”。 一公里多的路,他走得不快,却一步一步踩得扎实。 路过田埂时,看到地里的稻子长势正好,他停下来摸了摸稻穗,像抚摸着故乡的脉搏。 宗亲告诉他,这次不仅能扫祖父的墓,还能去看看家族最早迁到江西时的老祖先坟茔。 他一听就笑了,说这趟来得值,能替父亲了却心愿。 在村里的几天,他跟着乡亲们逛了新修的体育公园,去了黄庭坚故里,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景致,不住地感叹“变化太大了”。 有村民摘了村口枇杷树上的果子塞给他,黄澄澄的挂在枝上,甜津津的滋味在嘴里化开,他连忙用手机拍下来,说要发给在台湾的家人看看,“让他们也尝尝老家的味道”。 离开那天,车子驶在新修的乡村公路上,帅化民一直望着窗外。 他说,自己这一辈子,从对姓氏的困惑,到一步步踏上寻根的路,越来越明白,两岸的人说着一样的话,认着一样的祖宗,骨子里都是一家人。 那些所谓的隔阂,在血脉亲情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 他常跟人说,台湾的年轻人该多来大陆走走,别总听别人说,得自己亲眼看看。 就像他自己,走在奉新的土地上,摸着祠堂的柱子,吃着乡亲递来的枇杷,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根”。 这份根脉,不是谁能斩断的,就像村口的老枇杷树,年复一年结果,把甜滋味留给每一个回家的人。 帅化民知道自己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回来几次,但每次回来,都更坚定一个想法。 两岸的乡亲,本该像一家人那样往来,聊聊庄稼收成,说说孩子成长,那些复杂的纷争,在这些实实在在的日子面前,实在太轻了。 他把这些想法说给身边的人听,也把老家的变化讲给台湾的亲友,他觉得,只要多一个人明白这个理,两岸走近一步,就不难。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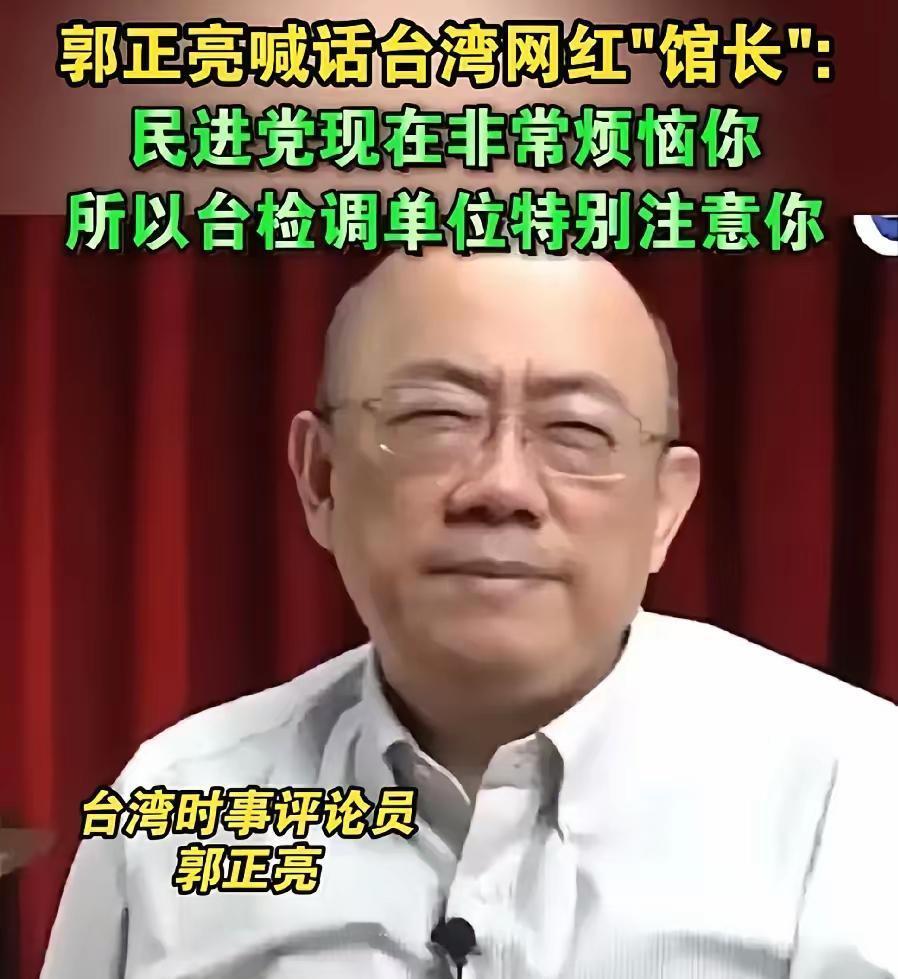








用户10xxx35
帅都化成民了,可是剑还没铸成犁,马也没有卸掉鞍。两岸还需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