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2008年,听了一辈子收音机的钱学森,突然跟儿子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多少钱?”儿子钱永刚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参考资料:2009-11-06 新华网——赤子丹心为中华——钱永刚追忆父亲钱学森的最后岁月) 钱学森,这位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百岁老人,彼时已是风烛残年,身体不再听使唤,他的听力衰退得厉害,连收音机里女播音员的高频声音也模糊成了噪音。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一生对电视毫无兴趣的科学巨匠,却在九十七岁那年的冬天,突然提出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请求:“支个电视行不行?” 他还反复向儿子钱永刚确认:“这东西要多少钱,贵不贵啊?”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究竟是他对新鲜事物骤然生起的好奇,亦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灵魂,在迟暮之年对信息获取方式的深切探寻?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学森便已从一线岗位退下,可他的思维广度丝毫未减,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系统科学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中,更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倡导学习、运用系统工程的热潮。 直到耄耋之年,他的心中仍系着宏大的理论构想与实践应用。 对他而言,日常接触的材料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系统科学的新理论、新观点及其在工程项目上的应用;二便是沙产业、草产业的理念,他会细致了解这些理念在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运用效果。 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系统工程理论在现实中的生动实践,他从不认为自己已登学术之顶峰,反而始终对新见解、新成就抱有浓厚兴趣,殷切期盼更多人能理解并运用他晚年的学术思想,由后辈们继续“冲锋陷阵”。 然而,这位战略家的目光,却远不止停留在理论的延续与深化上,他对国家发展中的“系统漏洞”有着极其尖锐的诊断,教育和人才培养,始终是他晚年心系的核心问题。 在中央领导探望时,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国内的大学没有一所是按照培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模式来办的,这导致学生们“不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不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大多流于人云亦云。 他痛心疾首地提醒道,这简直是教育体制的痼疾,如果国家不引起高度重视,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国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高质量的人才。” 更让他“不带劲”的,无疑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缺失,当儿子钱永刚告诉他,国产大飞机仍需购买外国发动机时,他虽然笑了,可那笑声中分明透着一股无奈与遗憾。 他紧接着追问儿子,发动机是放在翅膀底下还是机身里,有几个? 这些只有行家才懂的细节,足以显示他内心深处的关切,而当他看到汽车广告多是外国品牌,听说中国汽车也是“外国心”时,更是“泄气泄气”,不解地发出沉痛的追问:人都干什么去了? 即使如此心忧天下,钱学森的日常也透着一位普通老人的印记,他每日最主要的活动便是翻阅报纸,扫描标题,遇到感兴趣的便会让工作人员念出来;秘书也会每天送来期刊,他同样会翻阅一两本。 他始终心系国家大事,“报纸上大的事情他都知道,思想上还是蛮活跃的”,那么,那台他破天荒要求的电视机,并非仅仅为了消遣。 由于听力衰退,收音机里女播音员的高音他听不清,男播音员调门低反而听得清楚,因此,电视的到来,正是为了确保每日一定的信息输入,毕竟,“老爷子一直很关心国家发展”。 有时,看电视甚至让他“来劲”,儿子劝他躺下休息,他却说“还看一会”。 谁能想到,近百岁高龄的他,还能津津有味地看世界游泳锦标赛,那些花样游泳、跳水等动态画面,对他而言,不只是一般的娱乐,更是对眼睛的感官刺激,家人也因此尽量多陪他说说话,多刺激他脑子多动,希望以此延缓衰老。 在这些日常琐碎中,儿子钱永刚成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钱永刚带回的每一次见闻,都如同将他带到了现场,让他能及时了解、思考。 尽管记忆力已大不如前,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仍然常常回溯过往,他时常提起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重用,聂帅对他的信任,感谢他们给予他施展才华的巨大权力,让他能为中国的导弹事业奋斗。 而他更会感恩老师们的培养,特别是冯·卡门教授,正是老师传授的本领,才让他一生能为国家做些事情,这份对过往的铭记与感恩,与他对当下的深切忧虑交织在一起,显得尤为深刻。 他会问儿子:“现在中国有没有年轻一点、像我这样有名的科学家?” 当儿子坦率地告知,现在虽然有一些有名望的,但与他当年相比尚有差距时,这位老人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最终只平静而深沉地说了一句:“往前看吧。” 从一个支电视机的寻常细节,到对国产发动机、汽车自主创新的“灵魂追问”,再到“往前看吧”的深沉嘱托,钱学森的暮年生活,就像一部国家发展进程的缩影,一部关于思想者永不停止探索的史诗。 直至生命尽头,他都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用他独特的系统思考方式,为国家的未来把脉开方,即便生命之火微弱,忧国忧民之心却炽烈如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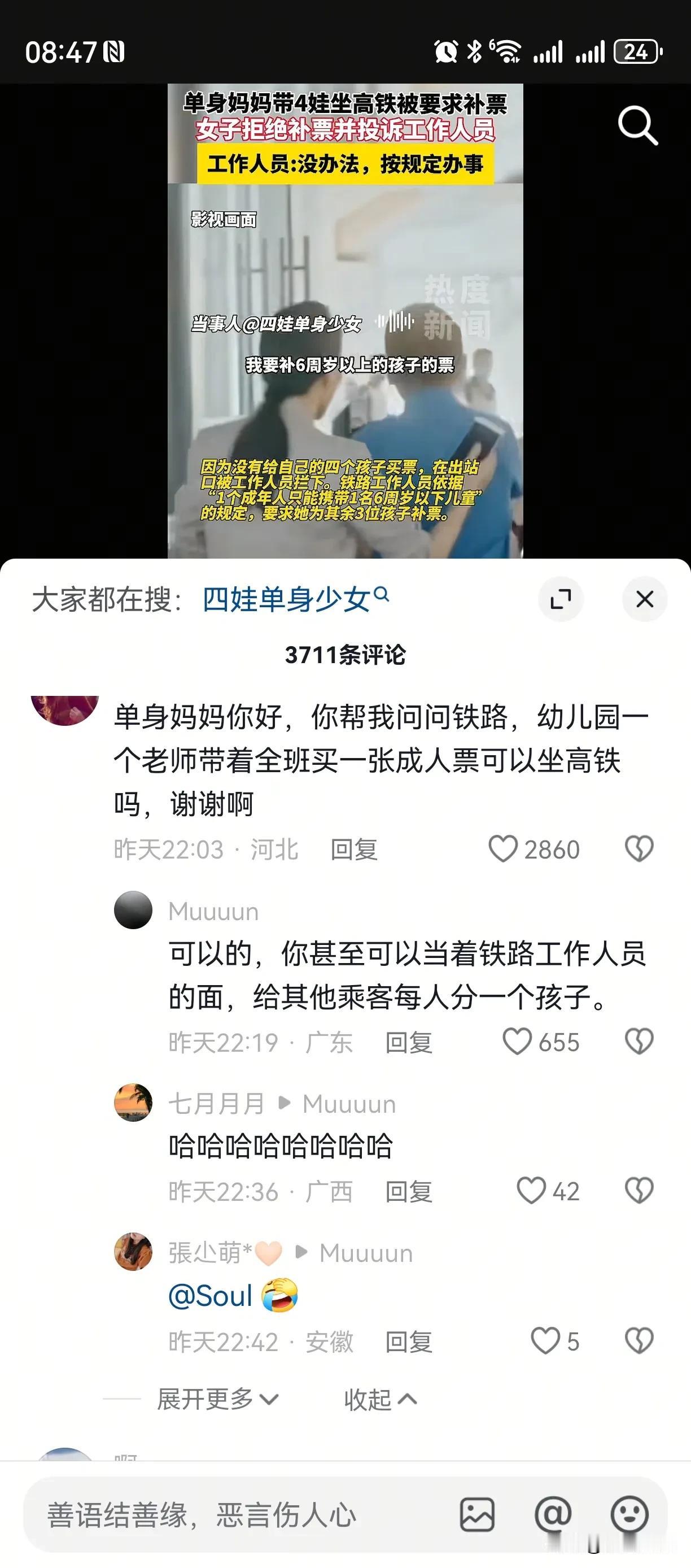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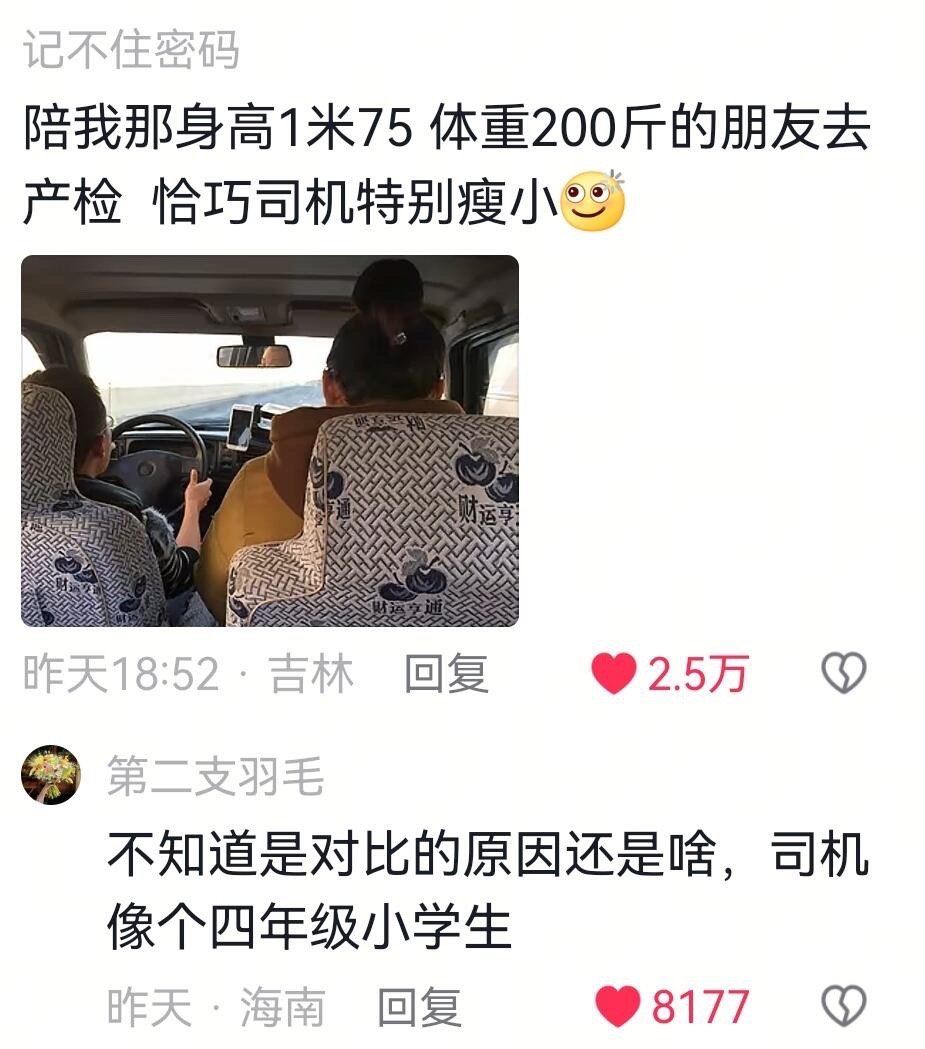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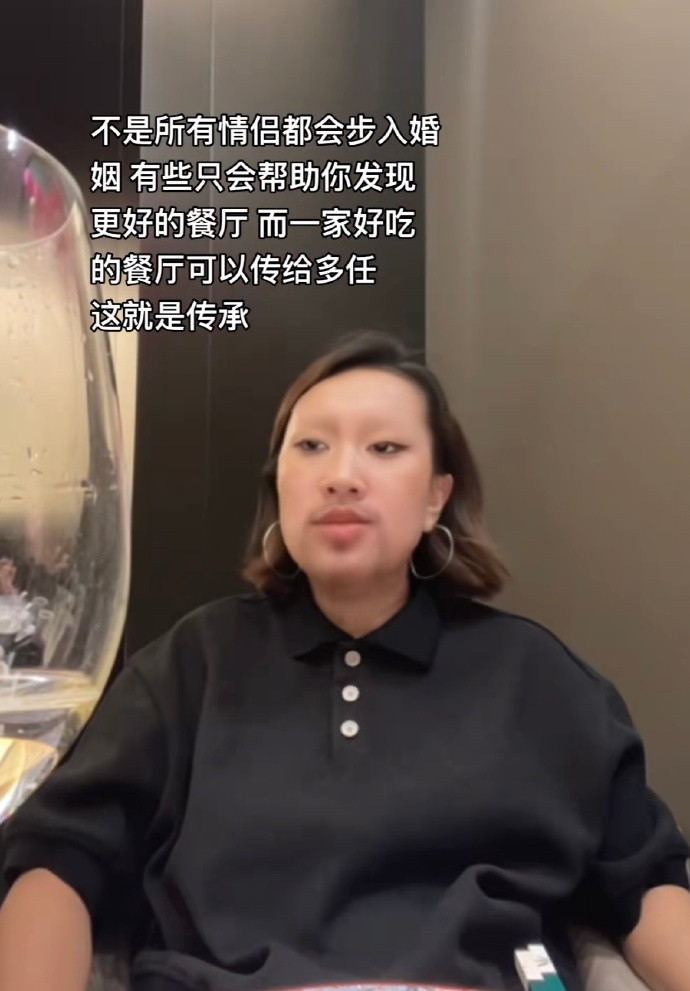
![[呲牙笑]工业国就是牛,随便搞搞就是一款“新型战术高机动输送车”——大家注意图](http://image.uczzd.cn/11707626222086064801.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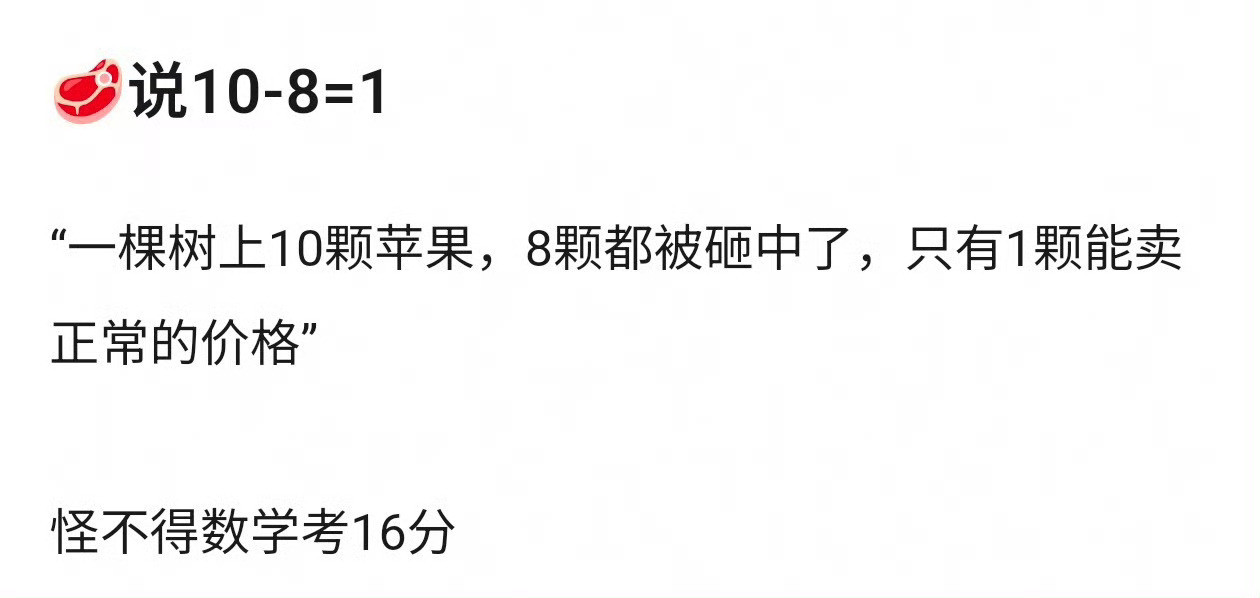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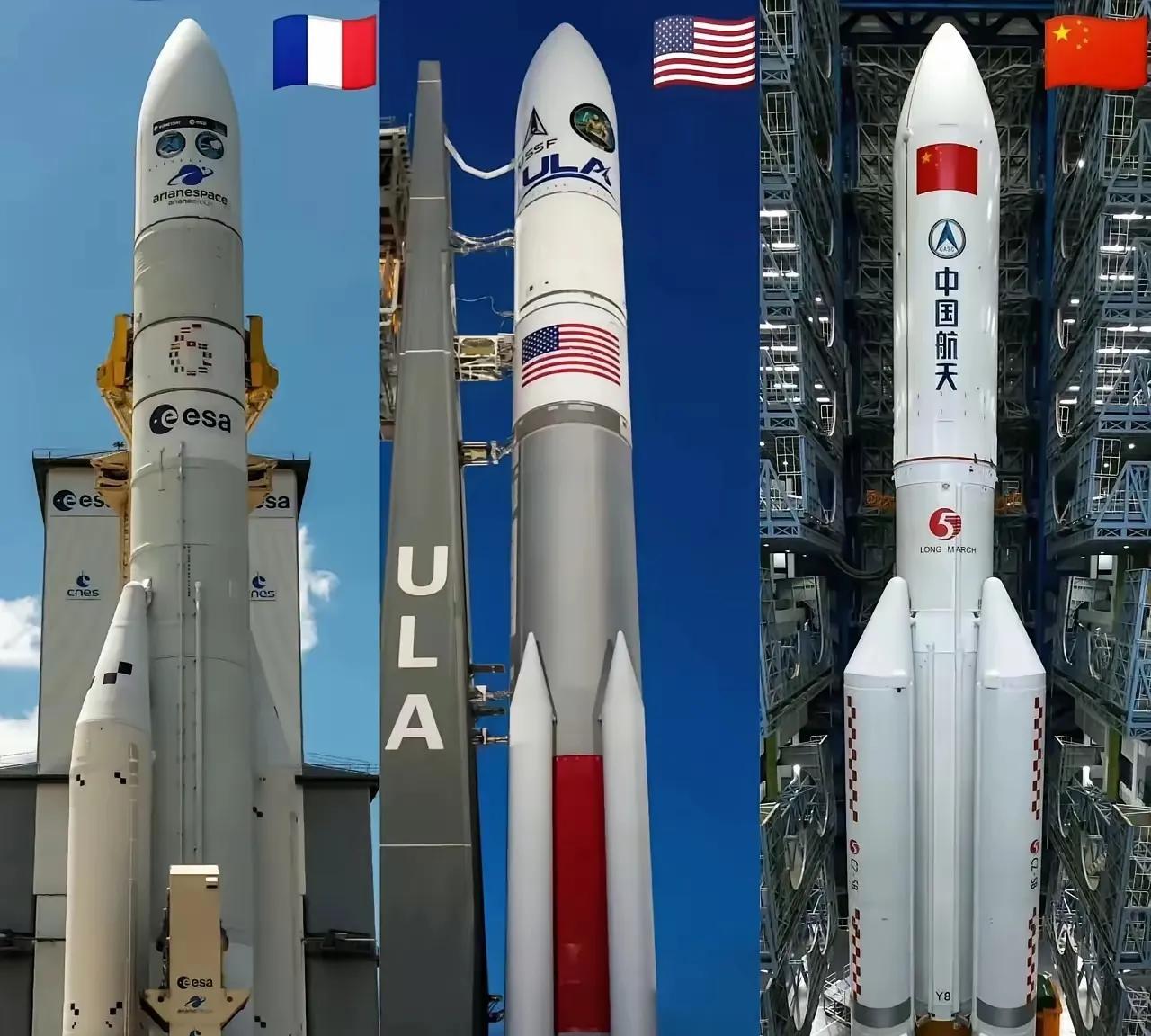


8538383
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