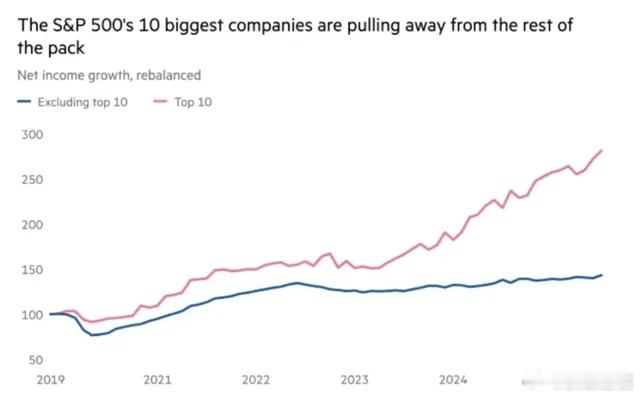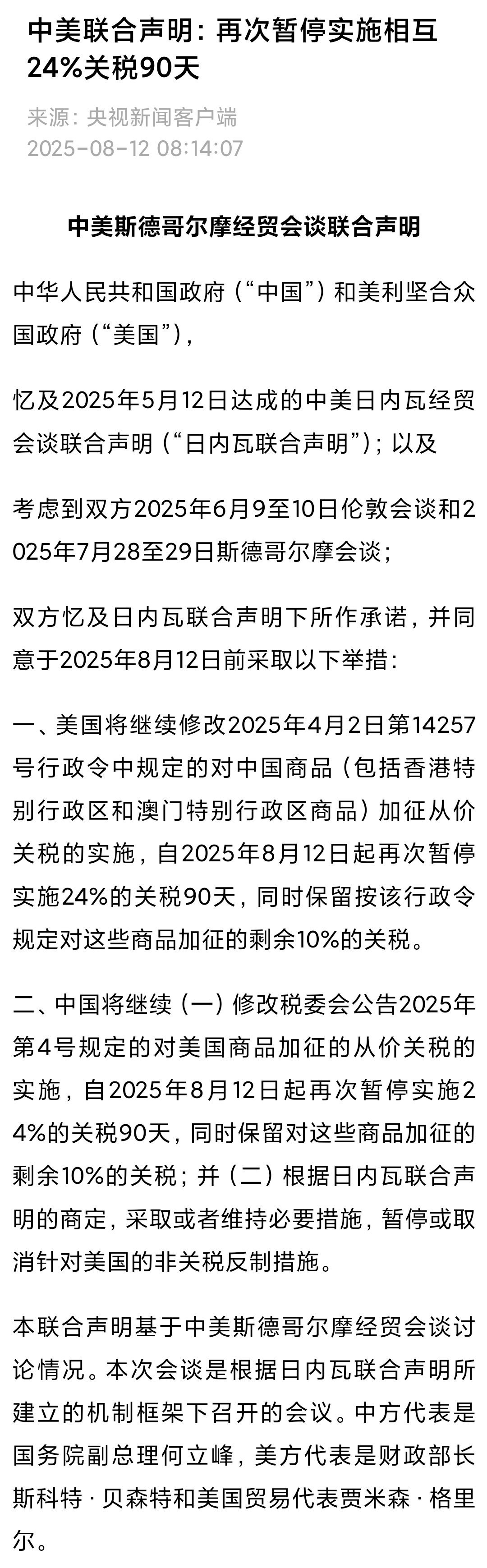8月12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上周公布的就业数据及本周二(8月12日)公布的通胀数据,再加上美联储更换一位理事,可为9月会议上大幅降息奠定基础。他希望参议院在9月美联储会议之前批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出任美联储理事。
按照以往规矩,美联储降息不需要联邦政府反反复复喊话。而特朗普当选之后屡屡督促美联储降息,这说明,美国决策者(特朗普行政班底)和金融市场“守望者”(美联储)已失去默契。一方面,联储主席鲍威尔担心特朗普凭空制造的关税战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匆忙降息将火上浇油;另一方面,特朗普对劳工统计局局长埃丽卡·麦肯塔弗8月1日发布的数据感到不满,索性解雇了麦肯塔弗。一方面,特朗普不满意这个数据——美国7月非农部门新增就业7.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5月和6月就业数据合计下调25.8万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贝森特又认为这一组数据有利于降息,他甚至认为,如果美联储当时掌握了修正后的数据(5月和6月就业数据),可能在6月和7月就降息了。
美国的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到底支持还是不支持降息,美国决策层的解读显得十分混乱。一方面,就业数据走弱,这还是美国过去几年反复调整就业数据统计方式后的结果,降息是最佳选择。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暗藏机关——8月12日公布的数据为: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7%,涨幅与6月持平;环比上涨0.2%,低于6月涨幅0.3%。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核心CPI同比上涨3.1%,涨幅高于6月的2.9%,并远高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的2%目标;环比涨幅为0.3%,为1月以来最大涨幅。从整体CPI涨幅看,通胀并不严重,而如果看核心CPI指数,就十分令人担忧了,降息时机并未到来。我认为,贝森特认为可以降息,主要考虑的是利息支出平衡,而非利率政策的科学使用。
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所以陷入如此境地,是美国过去数十年疯狂使用利率手段收割全世界的制度性反噬。货币政策主要管三件事: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就业水平。但有时需要有所取舍,三件事都兼顾到往往存在困难。美联储利率政策之所以在过去数十年“看上去很美”,在我看来,根本原因是美国的霸权效应使然。道理并不复杂:1)美联储利率政策被欧洲主要国家央行、欧洲央行、美国的亚洲主要盟国日本的央行,所充分吸收和传导,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动跟随,则美联储政策意图可以充分传导到全球经济体系。2)美国凭借其霸权机制,在全球布局跨国公司,在全球腾挪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分配利润。美国实体经济实际上依靠其他国家的经济来支撑,而利润分配主要由美国决定。如此,美联储“看上去很美”的利率政策,并不是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多么伟大,而是全球经济体系“簇拥”美国霸权的一种反映而已。3)当包括中国的新兴大国经济规模壮大之后,特别是与此相关的货币政策自我觉醒之后,美联储的传导效应逐步递减。在WTO机制下,贸易公平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向公平秩序转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逐步增强。4)全球性新冠疫情彻底打破了美联储在全球的金融霸权,美联储看似可行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叠加美债规模不可逆放大,最终造成其“本体经济效应”和“全球霸权效应”的高度扭曲,即高通胀、高利率、高经济成本同时存在。5)特朗普试图使用关税手段抢夺其他国家的GDP,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抵制,这进一步加剧了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尴尬。而稳定币等创新金融手段本质上是经济体系对美元投下的不信任票。因此,特朗普政府和美联储都显得十分纠结。特朗普政府与美联储主席之间的纠葛,更像是一场双簧戏,通过唱戏各自减压和逃避政治责任。特朗普本人尤甚。
接下来,美联储必然降息,这主要是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所需,而美国通胀、就业、GDP等数据大概率不会有很大改观。如果降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特朗普政府大可不必搞什么关税战。美联储降息总体上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一是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缩窄,有利于国内金融货币政策的腾挪;二是美联储神话被打破,有利于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三是凸显中国营商环境的稳定性,有利于中国金融和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