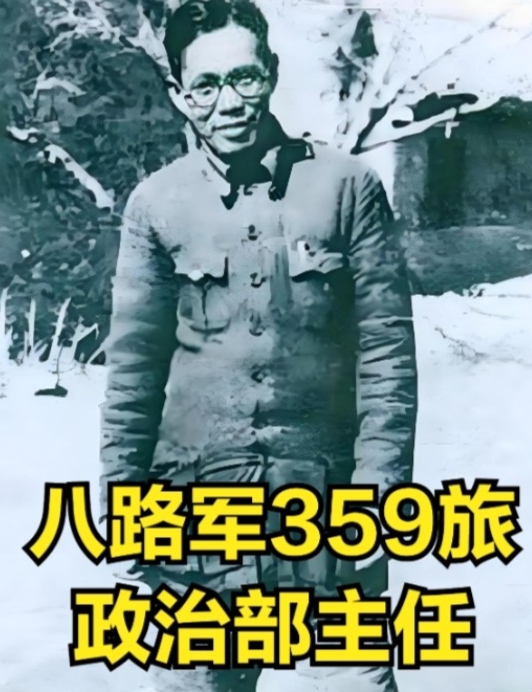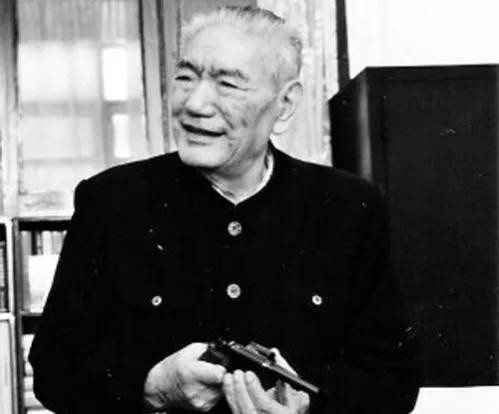1984年,战斗英雄杜海山被推上法庭被告席,妻子含泪控诉:"每月72块钱的工资,他只往家里寄6块,剩下的66块都给了谁?"法官正欲追问,杜海山突然沉声道:"我还得养活另外11个家。" 【消息源自:《解放军报》1984年系列追踪报道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84年民事案卷存档】 杜海山把那张皱巴巴的法院传票塞进军装内袋时,手心里全是汗。昆明六月的太阳毒得很,照得他眼前发黑。这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此刻站在法院门口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不停地用拇指搓着食指关节上那块枪茧。 "杜副连长,您爱人已经到了。"书记员探出头来喊他。审判庭里嗡嗡的议论声突然安静下来,李卫平坐在原告席上,攥着教案本的指节发白。他们结婚五年,这是妻子头回用这种眼神看他——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被告每月工资78元,为何只给家里6元?"法官推了推眼镜。杜海山听见旁听席上有军区的老战友在咳嗽,他盯着审判长背后那块国徽,喉结动了动:"报告,剩下的钱......都汇出去了。" 李卫平突然站起来,教案本啪地摔在桌上:"汇给谁?是不是在昆明养了别人?"她声音抖得厉害,鬓角有根白头发在阳光里特别扎眼。杜海山想起上个月妻子批改作业到凌晨,台灯灯泡坏了都舍不得换新的。 审判长敲法槌的声响惊飞了窗外麻雀。杜海山从内袋掏出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一张汇款回执。最上面那张寄往广西凭祥,收款人叫韦秀英,是烈士韦国强的寡妇,金额栏填着"5元"。 "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们班十二个人在凉山外围的山坳里抽了最后一包春城烟。"杜海山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得像在战壕里说悄悄话,"班长说要是谁活着回去,得照应其他人的爹娘。"他手指划过那些泛黄的汇款单,每张背面都用铅笔标着"张铁柱爹娘"、"王援朝媳妇"这样的字迹,有些地址改过三四遍——那些烈属总随着生计搬迁。 旁听席传来擤鼻涕的声音。李卫平慢慢坐回椅子,她突然想起丈夫总把"我们班"挂在嘴边,却从不说具体几个人。现在她知道了,那是个永远停在十二人的集体。 "为什么不告诉我?"李卫平问这话时,审判庭的吊扇正好停转,汗珠顺着杜海山的鬓角滑到领章上。他抿了抿嘴:"怕你担心......也怕那些家属难堪。"有回他偷偷给广西寄钱,碰见连里司务长,只好谎称是还老家赌债。 法官让书记员把汇款单拿去复印时,李卫平突然举手:"审判长,我撤诉。"她走到被告席前,把教案本里夹着的离婚协议书撕成两半。这个动作让她想起丈夫总把工资袋原封不动交给她,只是她从来没注意信封早就轻了一半。 三个月后,军区政治部的干事送来张表格:"老杜,现在国家有新政策,烈士抚恤金......"杜海山摆摆手打断他,窗外李卫平正领着几个战士家属在菜地摘茄子。他摸出兜里那包没拆封的春城烟,轻轻放在办公桌抽屉最里层。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