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朴树的母亲看着儿子窝在沙发上拨弄吉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你已经在家啃老5年了,要不要出去刷盘子养活自己?” 朴树抬起头,指尖还停留在琴弦上:“我写两首歌,包赚不赔。”
彼时的朴树25岁,房间里堆满了乐谱和磁带,墙上贴满了鲍勃・迪伦的海报。
这个出生在北大教授楼的年轻人,父亲是国际宇航科学院士,母亲是计算机专家,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相对论》和《空间物理学》,唯独他的床头柜上,常年躺着一把磨得发亮的木吉他。
父母不是没试过让他 “走正道”。高考那年,父亲把北大物理系的招生简章放在他桌上,他却偷偷报了中央音乐学院。
被发现时,他梗着脖子说:“做实验不如写歌有意思。”
最后拗不过他的倔脾气,父母只好任由他辍学在家,每天对着四壁创作。
那五年里,他很少出门,三餐靠母亲端进房间,唯一的社交是去胡同口的音像店淘打口碟。
有次父亲半夜起来,看见他还在灯下写词,烟缸里堆满了烟头,稿纸上划得密密麻麻。
带着那两首歌找到高晓松时,朴树的牛仔裤上还沾着颜料——前一天他刚给朋友的乐队设计完海报换了点零花钱。
高晓松在办公室里听完《那些花儿》的小样,突然站起来把磁带往录音机里又塞了一遍:“这歌里有股疯劲儿,是你自己写的?”
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当场拍板签约,转头就给老狼打电话:“我捡到宝了。”
朴树乐颠颠地跑回家报喜,母亲正在厨房熬粥,听完只是叹了口气:“能当饭吃吗?隔壁家的孩子都评上副教授了。”
他没反驳,默默把advance(预付款)存进银行,取了一部分给吉他换了套新弦。
那年冬天,他在录音棚里待了三个月,每天只睡四小时,出来时瘦得脱了形,却抱着母带笑得像个孩子。
2003年专辑《生如夏花》爆火,大街小巷都在放《白桦林》,朴树却突然消失了。
他把自己关在郊区的院子里,拒绝所有商演,连央视春晚的邀约都推了。
母亲去看他时,发现院子里种满了向日葵,他正蹲在地里拔草,手机扔在石桌上关机了。
“他们想让我唱一千遍《生如夏花》,可花儿谢了就该结果了。” 他擦着手上的泥说。
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14年韩寒敲开他的门。
这个同样特立独行的导演拿着《后会无期》的剧本:“我需要一首能让人想起远方的歌。”
朴树把自己关在书房三天,出来时递给他一叠纸,上面是《平凡之路》的歌词。
录音那天,他穿着旧 T 恤,唱到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时突然停下来,说要重录 —— 刚才的情绪里 “多了点世故”。
这首歌上线后,朋友圈被刷屏,有人说听哭了,有人专程去看电影只为听完整首歌。
商演报价翻了十倍,综艺邀约塞满邮箱,朴树却把手机设了拦截。
张亚东劝他趁热度发新专辑,他翻着乐谱反问:“写歌是为了赚钱吗?我现在有地方住,有吉他弹,够了。”
如今的朴树还是老样子,住在北京郊外的老房子里,窗帘常年拉着,书桌上摆着老式录音机。
有次歌迷在菜市场遇见他,他正蹲在地上挑土豆,说要回家炖牛腩。
有人拍视频发到网上,配文 “原来大神也吃家常菜”,他看到后只是笑笑,转头把royalties(版税)捐给了山区的音乐教室。
去年冬天,母亲去看他,发现他还在用那把旧吉他,弦轴都锈了。
“换把新的吧,现在条件好了。” 母亲说。
朴树低头拨了个和弦,声音温润如初:“这把有劲儿,像我。”
窗外的雪落下来,落在他当年写满歌词的稿纸上,那些曾经被质疑的梦想,终究在时光里开出了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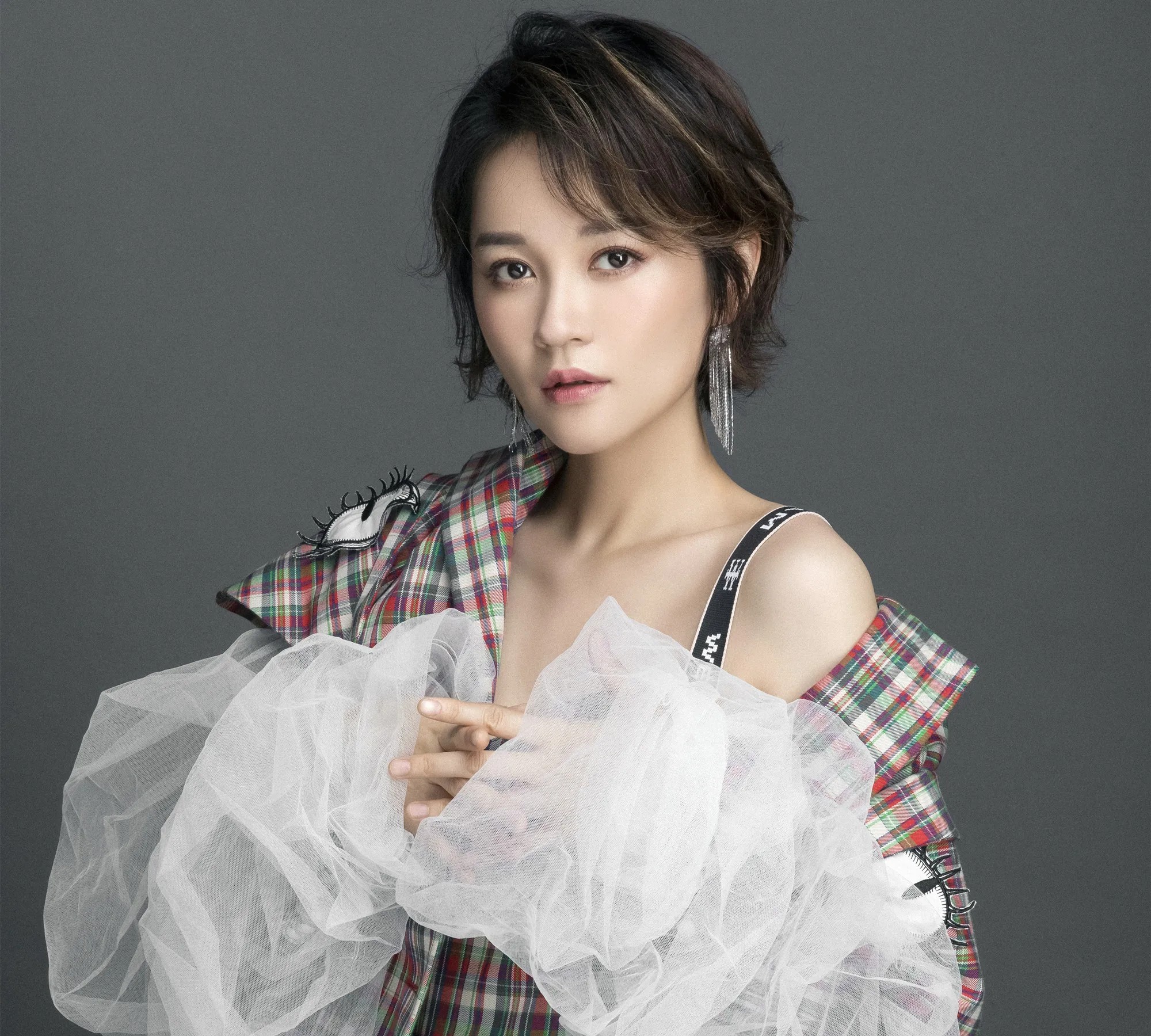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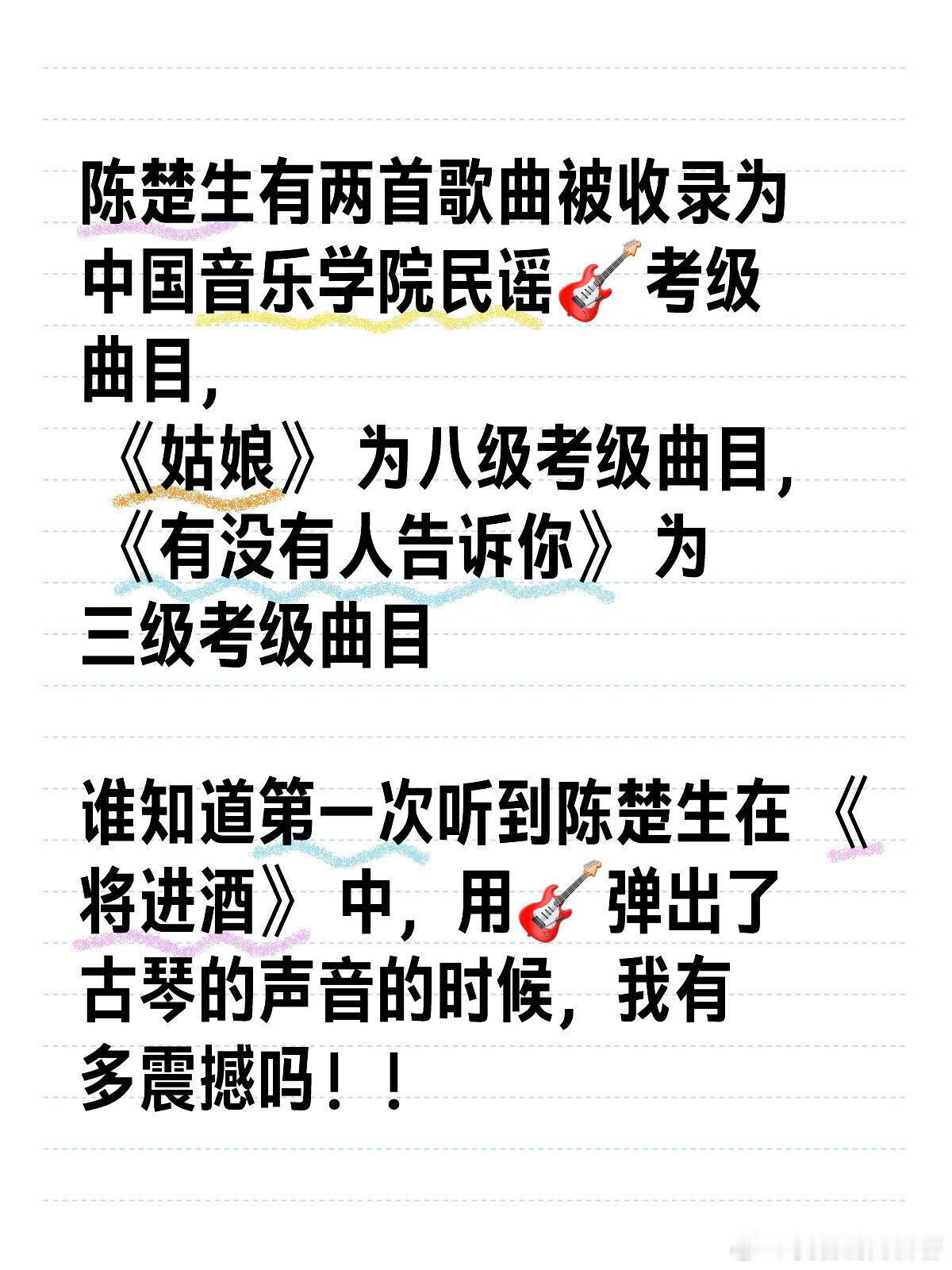



寻真
如此内心宁静的人,算是活的通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