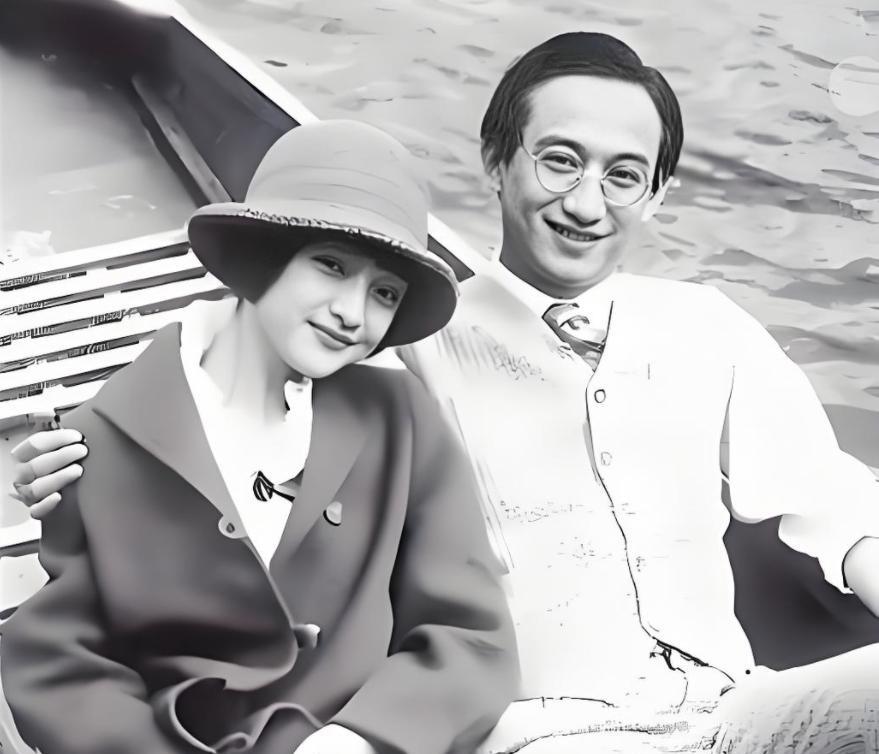徐志摩死后一年,徐父在给儿子遗孀陆小曼汇生活费时,写了这样的话:你既然已经和翁瑞午同居,那就不算我徐家儿媳,所以我将不再供养你。 信纸放在红木梳妆台上,旁边摊着半张未完成的画稿,墨痕洇了一角 —— 那是陆小曼学画的第三年,案头总摆着徐志摩生前用的狼毫笔,笔杆被摩挲得发亮。 1938 年的上海弄堂,翁瑞午抱着个锦盒走进陆小曼家。 盒子里是幅倪瓒的山水,他解开缎带时,指尖还沾着当铺的油墨印:“当了这个,够你买两个月的颜料。” 陆小曼没抬头,正用那支狼毫勾勒山石,笔锋抖得厉害。 她知道这画是翁瑞午的心头好,当年花了三百大洋从琉璃厂淘来的。 “何必呢。” 她轻声说,墨滴落在宣纸上,晕成个模糊的圆。 徐志摩生前的皮箱还在衣柜顶落着灰。陆小曼偶尔会踩个凳子翻下来,里面藏着他的讲课稿,字里行间总提到 “眉(陆小曼小字)要的那套进口胭脂”“眉说舞厅的水晶灯该换了”。 他在北大的月薪 580 大洋,加上《新月》的编辑费、上海的演讲酬劳,一个月最多能摸到上千大洋,比鲁迅多出两倍有余,却总在月底对着账单叹气。 佣人说,先生常躲在书房算钱,算着算着就把笔扔了:“不够,还是不够。” 翁瑞午的妻子陈明榴托人送来一叠小袄时,陆小曼正在给画题款。 布料是家常的蓝布,针脚细密,附了张字条:“天凉了,给重光做的,多出来两件,你试试。” 重光是翁家小女儿,去年来住过几天,嫌她屋里烟味重,半夜哭着要回家。 陆小曼摸着小袄的领口,突然把烟枪塞进了抽屉最深处 —— 那是翁瑞午特意托人从云南弄来的烟膏,此刻在她手里,竟有些烫。 1941 年的画展上,陆小曼的《秋江独钓图》前围了不少人。她穿件素色旗袍,鬓角别着朵白菊,站在画旁接受采访。 记者问她为何突然学画,她往人群后看了眼 —— 翁瑞午正帮她整理画框,袖口磨破了还没补。 “是朋友逼的。” 她笑了笑,“他说,总不能一辈子靠着回忆过活。” 那天卖出的画钱,她分了一半给翁瑞午,让他赎回那幅倪瓒山水,他却摇头:“留着给你买好颜料。” 上海文史馆的办公室里,陆小曼的笔筒里插满了新笔。1956 年她来这儿当馆员,每月 60 元工资,够自己糊口了。 同事劝她:“现在能独立了,该和翁先生说清楚了。” 她没接话,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个小匣子,里面是枚翡翠镯子,内壁刻着 “壬午年赠眉”。 1942 年,翁瑞午丢了工作,当掉传家宝换了这笔钱,给她请了最好的画师教画。 1961 年冬天,翁瑞午躺在病床上,拉着陆小曼的手数家里的古董:“那对官窑瓶子,留给你换汤药钱;还有那幅石涛,别当,留着压箱底。” 她点点头,给他掖了掖被角,像当年他陪她熬夜作画时,总替她披上的披肩。 第二年春天,陆小曼也病了,弥留之际,她让护士把徐志摩的诗集放在枕边,封面都磨卷了边。 最后送葬的人里,有翁瑞午的女儿重光。她按照遗嘱,把那支徐志摩的狼毫笔放进了骨灰盒。 有人问陆小曼这辈子究竟爱谁,重光想起小时候偷看到的场景:母亲陈明榴在厨房炖鸡汤,让她给陆小曼送去。 翁瑞午蹲在陆小曼画室门口打盹,手里还攥着给她买的海棠糕;而陆小曼的画稿里,总藏着个模糊的背影,有时像徐志摩,有时像翁瑞午。 徐申如那封信后来被陆小曼夹在了徐志摩的诗集里。多年后有人翻开,看见信纸背面有她的小字: “他(徐志摩)给了我热烈的火,他(翁瑞午)给了我温吞的炭,火燃尽了,炭却暖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