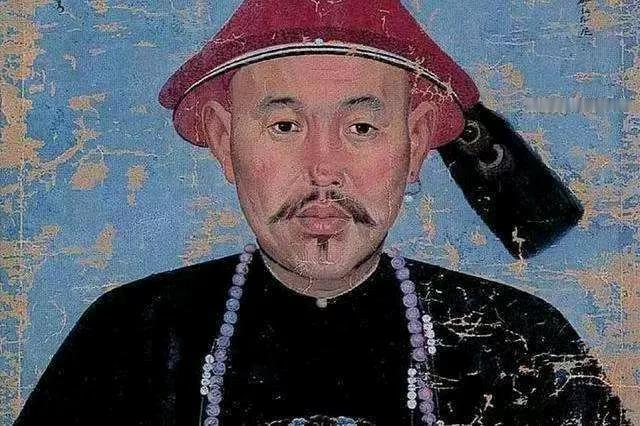乾隆十一年五月十三,乾隆叫了纪晓岚一起去看庙会。在街上遇到个卖馄饨的女人,乾隆问那女人:“老板娘,你当家的呢?”。那女人牛高马大,嗓门儿也响,说:“那死鬼的身板儿还不胜我呢!他起得早,剔骨头时削了手指头,寻郎中包裹去了,顺便再买些作料。 乾隆那天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透,便唤了纪晓岚一道儿出门,说是“去瞧瞧热闹”。京城庙会年年有,但皇帝亲自上街的次数,可不多。纪晓岚心里明白,这不是闲逛,这是微服私访,皇上要借这个机会摸摸底,看看老百姓过得怎么样。 庙口的幡旗被风扯得哗哗响,卖糖画的老汉正用铜勺在青石板上勾龙凤,甜香混着油条的油气飘过来。乾隆穿着件月白长衫,袖口磨得发毛,活像个家底殷实的读书人,只有那双眼睛,总在不动声色地扫过周围——看路边摊贩的幌子新不新,听茶棚里说书人讲的是前朝故事还是坊间疾苦。 “客官要几碗?”卖馄饨的女人挥着大铜勺,锅里的白汤“咕嘟”冒泡,浮着层金黄的油花。她胳膊上的青筋随着动作鼓起来,围裙上沾着点点油星,却洗得发白。 乾隆往条凳上一坐,木凳“吱呀”响了声:“来两碗,多加葱花。” 女人应着,手没停。笊篱捞起馄饨往碗里倒,又从瓦罐里舀出半勺虾皮,动作麻利得很。“您二位是外乡来的吧?”她嗓门亮,盖过了旁边耍猴的锣声,“今儿庙会人多,昨儿个我家那口子就说,得提前两时辰起火烧水,偏他不中用,切个肉都能伤着手指头。” 纪晓岚在旁赔笑,眼角却瞟着乾隆。皇上正盯着女人脚边的竹筐,里头码着整整齐齐的碗,每个碗沿都擦得锃亮。 “日子过得还行?”乾隆啜了口汤,热辣辣的暖意从喉咙淌下去。 女人“嗤”了声,把铜勺往锅沿一磕:“饿不着,也富不了。一碗馄饨五个大钱,除去面、肉、柴火,一天挣的够买二斤米,再给娃扯块粗布做件褂子。”她顿了顿,往远处瞅了眼,“就是税银再少点就好了,去年冬天雪大,煤价涨了三成,税银一分没减,差点没撑住。” 这话像颗小石子,在乾隆心里荡开圈儿。他想起上月户部递的奏折,说“京畿百姓安居乐业,赋税征管有序”,可眼前这女人的话,糙是糙,却比奏折上的字实在多了。 “税银重?”乾隆放下碗,指尖在桌沿轻轻敲着。 “也不是重得活不成,”女人挠了挠头,倒有些不好意思,“就是……当官的来收税时,总爱多要俩钱买酒喝。说是什么‘辛苦费’,咱小老百姓,哪敢不给?” 纪晓岚心里一紧,刚要岔开话,却被乾隆按住手。皇上脸上没什么表情,只问:“哪个衙门的?” 女人摆手:“那哪记得清?穿身官服就来了。不过啊,比起前几年,强多了。”她舀了勺汤续进乾隆碗里,“听说新皇上登基后,杀了几个贪钱的官,去年冬天,还有官爷给咱送过棉衣呢。” 太阳慢慢爬高,照在馄饨锅上,油花闪着碎金似的光。乾隆付了钱,临走时多看了眼那口锅——锅底结着层薄薄的垢,却干干净净,想来是天天擦洗。 往回走的路上,谁都没说话。过了街口,乾隆才慢悠悠地说:“纪昀,你说,这折子上的话,和这锅里的汤,哪个更真?” 纪晓岚答:“汤里有盐,话里有假。” 皇上笑了,笑声里带着点自嘲:“是啊,盐放多了发苦,话说得太满,就成了空话。”他想起那女人说“饿不着,也富不了”,想起她擦得发亮的碗,想起她提到“新皇上”时眼里的盼头。这些,都不是奏折里“安居乐业”四个字能装下的。 回宫后,乾隆没提这事,只下了道旨:严查京畿地区税银征管,凡有额外勒索者,立斩。又让人按市价,给各州县的税吏加了两成俸禄,附了句话:“俸禄够了,就别再惦记百姓碗里的馄饨。” 后来纪晓岚偶尔想起那天,总记得那碗馄饨的热乎气,还有女人说“娃等着新褂子”时,眼里的光。那光,比宫里的琉璃灯亮多了,也实在多了——它照见的,才是真正的日子。 信息来源:据《清高宗实录》《阅微草堂笔记》等记载,乾隆年间常有微服私访之事,民间亦多有相关传说。本文细节参考清代《燕京岁时记》中关于庙会的记载,及《清史稿·食货志》中对当时赋税的记录,旨在反映帝王与民生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