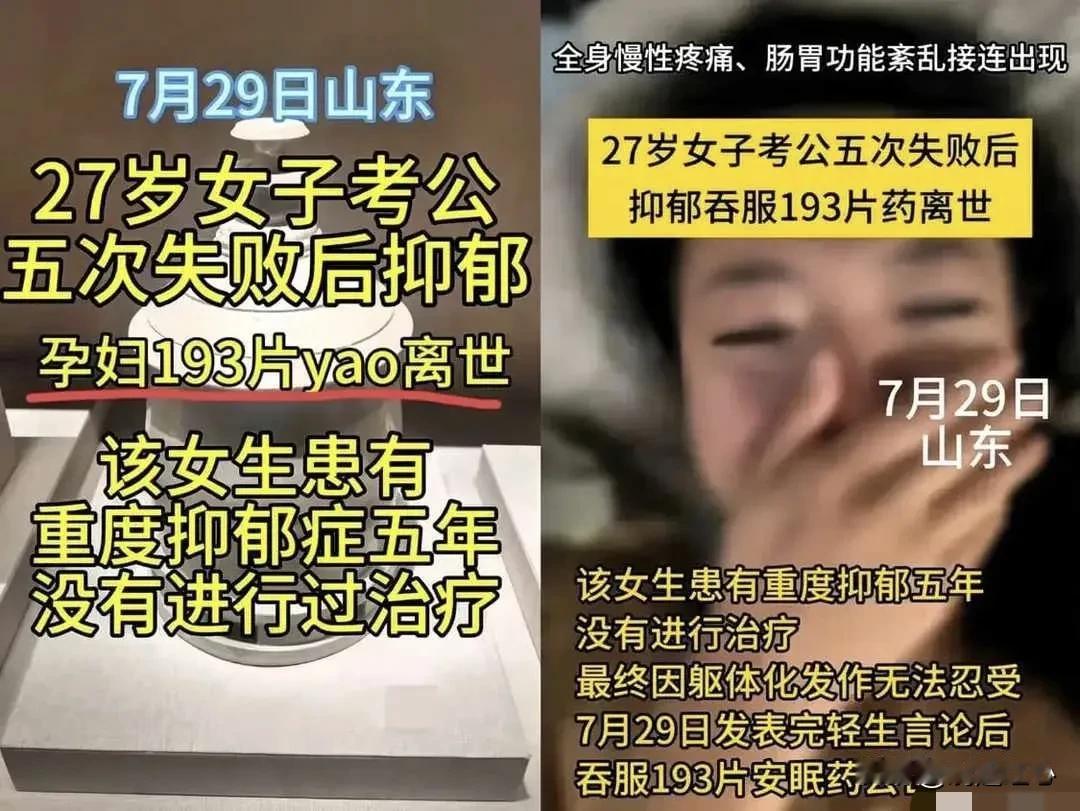1971年,陕西一位朴实的老农迎娶了比自己年轻十岁的女大学生,她曾身陷囹圄又历经婚变,老农却始终不离不弃。谁曾想八年后,妻子突然恢复身份重获公职,老农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竟捡到了天大的福分! 【消息源自:许燕吉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南京农业大学校史档案(1970-1980年卷);陕西省武功县地方志(婚姻家庭篇)】 197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陕西武功县的老魏蹲在自家土坯房门口,手里捏着那张盖着红戳的平反通知书,纸页被汗浸得发软。他扭头朝屋里喊:"孩他娘,这上头写的啥?你给念念清楚。"许燕吉在围裙上擦着手走出来,阳光斜斜地照在她早生的白发上,那些字突然就模糊了。 八年前也是这样刺眼的阳光。生产队长领着个穿补丁衣裳的女人站在麦场边上,说这是城里来的"右派分子",要老魏"帮着改造"。四十八岁的光棍汉搓着皲裂的手掌,看见女人脚上的塑料凉鞋已经裂了口子,露出冻得发青的脚趾。"会喂猪不?"他问。女人低着头:"没喂过,但能学。"就这五个字,带着南京人特有的软糯尾音,像片羽毛落在黄土高原干裂的地皮上。 婚礼简单得寒酸。老魏用半布袋玉米换了两斤散酒,许燕吉把唯一的呢子外套染成藏青色当喜服。村里人蹲在墙根下嚼舌根:"魏瘸子捡个女特务""听说她爹是反动学术权威"。洞房夜,煤油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老魏突然说:"俺知道你不是坏人。"许燕吉正铺被褥的手顿了顿,被角上补着块蓝布,针脚歪歪扭扭——这是她蹲牛棚时学会的手艺。 最难熬的是头年冬天。许燕吉半夜被冻醒,发现老魏把整床棉被都裹在她身上,自己蜷在炕角盖着件破羊皮袄。天亮时她看见灶台边堆着新劈的柴,老魏的棉裤膝盖处结着冰碴——他天没亮就上山砍柴去了。开春教识字,她握着继子黑乎乎的小手在沙地上划"人"字,孩子突然仰头问:"娘,城里人写字都用金笔吗?"许燕吉喉头一哽,想起父亲送她的派克钢笔早被抄家时折成了两截。 1976年深秋,老魏从公社回来脸色发青。许燕吉正在纳鞋底,针尖戳破了手指。"他们说...说你爹是人民作家?"他憋出这句话时,许燕吉手里的顶针咣当掉在地上。那晚她第一次说起许地山,说香港大学的洋教授,说《落花生》课文怎么被选进小学课本。老魏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俺就晓得,能写出'要做有用的人'的,准不是坏人。" 现在这张平反通知书就摊在炕桌上。老魏盯着妻子颤抖的睫毛:"你要回南京?"许燕吉把通知书折好塞进他口袋:"咱家的自留地该种春玉米了。"但夜里她听见老魏在院里磨了整夜的镰刀,月亮照得磨刀石发白。 转折发生在谷雨那天。继子举着录取通知书冲进院子:"爹!娘!我考上西北农学院了!"老魏把儿子举过头顶时,许燕吉看见他藏了半辈子的眼泪终于砸在黄土里。当晚老魏突然说:"俺跟你去南京。"许燕吉正在补袜子,线头啪地断了:"你可想好,城里没自留地。""俺会看自行车棚。"老魏咧着嘴,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 1980年南京的夏天热得反常。农科院的同事总看见个陕西老汉蹲在实验田边上,拿小本本记"啥时辰浇的水"。许燕吉在办公室翻译外文资料时,老魏就坐在传达室给她的搪瓷缸子续热水。有次他神秘兮兮地拉她看阳台:"俺用花盆种出小米了!"青黄的穗子支棱在仙人掌旁边,像出滑稽戏。许燕吉笑着笑着就哭了——在武功县时她总嫌小米粥拉嗓子。 2006年老魏走得很突然。临终前他盯着病房窗外的梧桐树说:"这树比咱家后山的枣树高多咧。"许燕吉握着他布满老茧的手,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个问题:"会喂猪不?"她俯身在他耳边说:"老魏,我学会喂猪了。"心电监护仪上的波浪线渐渐拉直,变成一马平川的黄土高原。 2014年冬天,82岁的许燕吉在遗体捐献公证书上签完字,突然问护士要了张白纸。她工整地抄下《落花生》最后一段:"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墨水有些晕开,像被黄土吸走的晨露。窗外梧桐树的影子投在纸上,枝枝叉叉都是岁月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