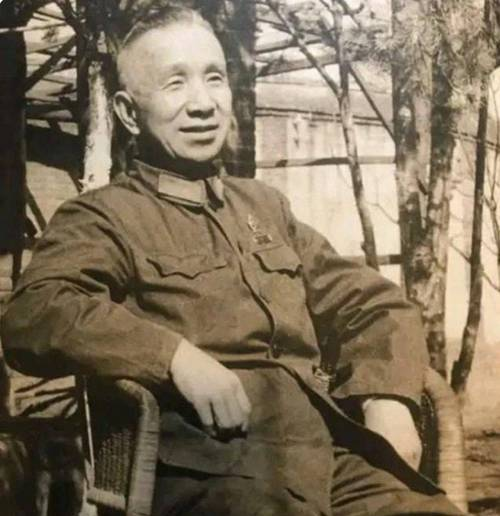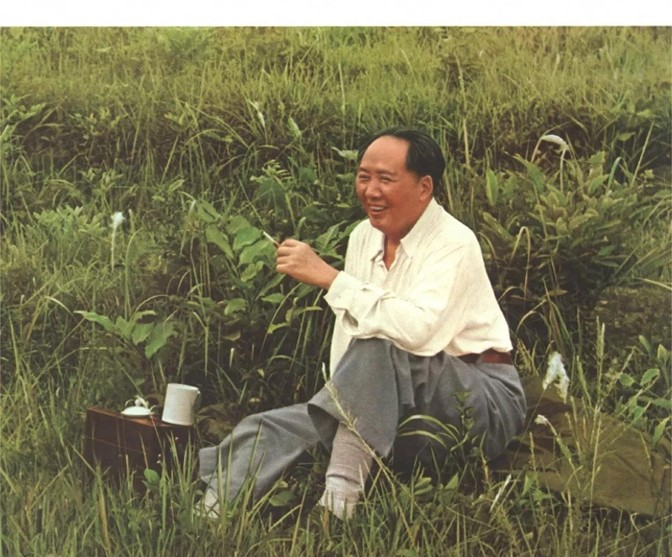1949年,陈毅到上海一家面馆用餐,正吃着面时,进来一老农并点了一碗阳春面。不料,老农面条上来后,陈毅拍桌而起:“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
1949年,陈毅换上普通灰布衫,带着秘书小王走进黄浦江边一家挂着“老张面馆”招牌的小店。
店内烟雾缭绕,十几张油腻的方桌坐满了码头工人和小商贩,跑堂的是个精瘦中年人,看见陈毅进门立刻迎上来,嗓门特别大说这儿阳春面最有名!
陈毅点了两碗阳春面,选了靠墙角的位置坐下,面条很快端上来,白瓷大碗里堆着厚厚的面条,肉丝葱花铺了满满一层,汤头浓白香气扑鼻。
正准备动筷子时,门帘一掀,进来一个穿着打补丁蓝布衫的老农,老人弓着腰,裤脚还沾着黄泥,小心翼翼在门边找了个空位坐下。
老农轻声叫了一句,师傅,来碗阳春面,跑堂的皱着眉头走过去,俯身听了几句,转身朝后厨大喊,十一一碗!
刚才给陈毅下单时,跑堂的喊的是“一十一碗”,陈毅心里一动,继续观察。
十分钟后,老农的面条端上来了,同样的白瓷碗,里面却只有半碗清汤,几根面条稀稀拉拉沉在碗底,连葱花都只有几片。
陈毅放下筷子,起身走到老农桌前,指着两个碗问跑堂的,同样是阳春面,为什么分量差这么多? 跑堂的一愣,支支吾吾回答,这个......客官您不懂,面条有好几种做法。
陈毅追问价钱,跑堂的声音越来越小说着价钱是一样的。
周围食客渐渐围拢过来,陈毅提高声音,我刚才听你喊单,给我们是'一十',给这位老师傅是'十一',什么意思? “跑堂的脸刷地红了,眼珠乱转不敢答话,这时后厨走出个胖厨师,陪着笑脸解释,”'一十'就是好料足,'十一'是普通做法。
陈毅冷笑,普通做法就是欺负老实人?同样的钱,凭什么给人家半碗汤?
老农这才明白过来,颤抖着站起身,说着不吃了,就要往外走。
陈毅拦住他,老师傅别走,您该吃的面一口不能少,然后转向店老板,重新给这位师傅做一碗,按这个标准做。
面馆老板这时从后面匆匆赶来,一看这阵势知道遇上硬茬了,连声道歉,亲自下厨重做了一碗货真价实的阳春面。
第二天,工商所的人就来了,带着陈毅一起重新检查这家面馆,原来“一十”是上海滩的黑话,指当官的或有钱人,“十一”指普通百姓,不光这家面馆,很多小店都有类似暗号。
面馆被勒令整改,必须明码标价,不准区别对待顾客,一周后重新开业,墙上贴着清楚的价目表:阳春面统一两毛钱,用料标准一样。
这件事在附近街坊中传开了,有人说那个穿灰布衫的客人就是新市长陈毅,也有人不信,但大家都发现,周围的小店开始改规矩了。
菜场里,摊贩不再看人穿着决定菜品好坏,布店里,伙计也不敢再用鼻孔看衣着普通的顾客,连黄包车夫都说,拉车时被小店老板客气对待的次数明显多了。
一个月后,陈毅又去了那家面馆,换了新跑堂的,一碗阳春面端上来,分量足料也实在,他特意观察了其他桌的客人,一个拾荒老人和一个穿长衫的先生,碗里的面条分量一模一样。
那个被欺负的老农后来专门托人带话给陈毅,说自己种了一辈子菜,头一回在城里被人当人看,他不知道那天帮他的是市长,只知道上海滩开始变样了。
从面馆的暗号到明码标价,从看人下菜碟到一视同仁,这座城市在细节中完成着蜕变,普通人第一次发现,花同样的钱能买到同样的东西,这在旧上海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老张面馆的故事传遍了整个黄浦区,人们开始明白,新社会不只是换了旗帜和口号,更要换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偏见和习惯。一碗阳春面的分量,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对公平的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