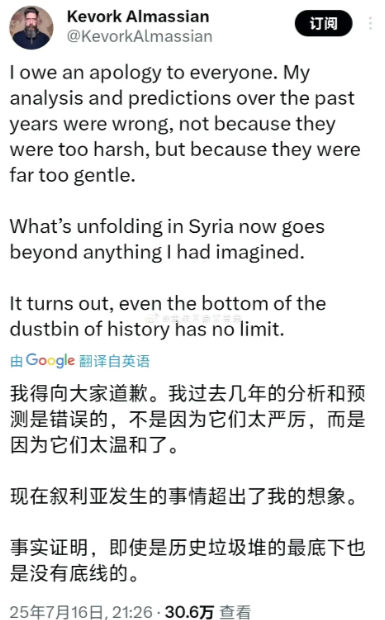沙特王子车祸沉睡 20 年后去世,而作为王室成员,他沉睡期间,依然享有每月 27 万美元的津贴,并持续调用医疗资源。 利雅得皇家医院的特护病房里,监护仪的长鸣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护士长阿依莎看着屏幕上那条平直的绿线,轻轻叹了口气 —— 这位沉睡了 20 年的王子,终究还是没能等来奇迹。 1995 年那个沙尘暴肆虐的午后,24 岁的王子驾驶着限量版跑车在沙漠公路上失控,颅脑重创后陷入深度昏迷,从此成了这间病房里永恒的 “住客”。 病房的陈设 20 年未变:埃及棉的床单每天更换,黎巴嫩雪松精油的香气终年弥漫,墙上挂着他车祸前赢下马术比赛的照片,笑容里还带着未脱的稚气。 最显眼的是墙角那排精密仪器,从德国进口的脑电波监测仪每小时生成一份报告,瑞士定制的呼吸机按照他青年时的呼吸频率调节参数,连静脉营养液都由巴黎的营养师每周远程调配配方。 8 名护士轮班值守,每个人都记得王子左手臂上有颗小小的朱砂痣,那是为了在日常护理中避免静脉穿刺失误特意标记的。 这些开销的账单,最终都流向了王室财政。按照沙特 1950 年确立的王室津贴制度,无论成员健康状况如何,每月的基本津贴一分不少。 王子的账户里,每月 1 日都会准时汇入 27 万美元,20 年累计的 6500 多万美元,一部分用于支付医疗团队的薪酬 —— 光是神经科专家的年度会诊费就高达 50 万美元,另一部分则投入了 “植物人促醒研究”,资助了全球 12 个实验室的相关项目。 有次阿依莎无意中听到王室管家打电话,说要从日本空运一种新研发的干细胞制剂,单支价格够普通沙特家庭支付 10 年房租。 而在利雅得城南的平民医院,48 岁的清洁工法蒂玛正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抉择。她的丈夫三年前中风昏迷,每天的 ICU 费用相当于她三个月的工资。 起初她变卖了首饰和嫁妆,后来不得不向慈善机构求助,可当医院通知需要更换新的呼吸机时,她看着账单上的数字,终究在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了字。 “真主会原谅我的,” 她在丈夫的病床前祈祷,指尖划过他冰冷的手背,“我们实在负担不起了。” 拔管那天,法蒂玛发现丈夫的指甲缝里还留着清扫医院走廊时沾的灰尘,那是他最后为这个家劳作的痕迹。 王子的父亲,那位曾执掌沙特石油部的亲王,从未动摇过救治的决心。 他拒绝了所有医生 “脑死亡不可逆” 的建议,甚至在 2010 年斥资 2000 万美元,为医院修建了专属的直升机停机坪,确保任何时候都能在 15 分钟内召集全球顶尖专家。 有次一位年轻医生私下建议 “或许该考虑患者的尊严”,立刻被调离了特护团队。 在亲王的认知里,维系儿子的生命,不仅是父爱,更是王室权威的象征 —— 哪怕只是维持着呼吸,这位王子也是沙特庞大特权体系里不能熄灭的一盏灯。 这种极致的投入,渐渐催生出一条隐秘的产业链。 德国的医疗器械公司为王子定制了防褥疮的智能床垫,荷兰的花卉商每周空运最新鲜的沙漠玫瑰,连美国的好莱坞道具师都被请来,用特殊材料制作王子的 “仿真皮肤”,让他在王室成员探视时看起来更 “体面”。 这些围绕着 “沉睡的生命” 运转的产业,养活了成百上千的人,却也让利雅得贫民窟的居民在茶馆里叹气:“亲王用石油换来的钱,填进了一个永远醒不来的梦。” 20 年里,病房外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 沙特的年轻一代开始讨论女性驾车权利,社交媒体上有人质疑王室津贴的合理性,连医院里的护士们私下也会嘀咕:“这些钱如果用来建平民诊所,能救多少真正能醒来的人?” 但只要亲王的车队还会每月出现在医院门口,这些议论就只能消散在沙漠的热风里。 王子去世那天,他的床头柜上还放着刚送来的津贴支票。 阿依莎收拾遗物时,发现枕头下藏着一本 1994 年的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想去北极看极光,不带保镖,就自己去。” 她忽然想起,有次亲王来探视,摸着儿子的头发说:“等你好了,爸爸送你一艘游艇。” 那时监护仪的波形微微跳动了一下,没人知道那是仪器的误差,还是一个被困在黑暗里的灵魂,听到了这句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葬礼按照王室礼仪举行,耗资千万的仪式上,白袍的王室成员们整齐肃立。而在城南的平民公墓,法蒂玛为丈夫立了块简陋的石碑,上面只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风吹过两处墓地,一处飘着名贵的乳香,一处扬着干燥的沙粒,却都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生命终究会走向终点,只是有些人的终点,被特权铺成了漫长而奢华的甬道,而另一些人,只能在现实的重压下,选择最朴素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