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元年,宦官童贯出使辽国,遭到辽国天祚帝的耻笑“南朝乏才如此!”当晚在宴射场上,童贯对一个随行文官说了几句,此人竟一举震惊辽国——只见这个叫张叔夜的瘦弱文官一支雕翎箭破空而出,百步外鎏金箭靶正中红心!辽主举杯的手僵在半空,群臣的笑容凝在脸上。《宋史》载此幕时仅几字:“叔夜先中的,辽人诧异。 那支箭钉在靶心的闷响,像块石头砸进结冰的湖面。宴射场里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旌旗的簌簌声,刚才还在窃笑的辽官们,嘴巴张着忘了合上。有个捧着酒壶的侍从手一抖,琥珀色的酒液溅在锦缎地毯上,洇出深色的印子,他却浑然不觉。 童贯原本捏着酒杯的指节泛白,这会忽然松了劲。他扭头看张叔夜,见这人刚放下弓,袍角还沾着点草屑,脸上没什么得意的神情,倒像是刚写完一篇策论那样平静。童贯想起白天在辽主殿上,天祚帝斜着眼说“南朝乏才”时,满殿辽臣的哄笑,那笑声像针一样扎在他背上。他当时只能干笑,心里却憋着股火,傍晚见张叔夜跟着队伍,想起这人是随行的秘书少监,随口提了句“若能露一手,也算挣回些体面”,哪想到真成了。 张叔夜其实早把弓握热了。他出身将门,父亲张耆是仁宗朝的武将,家里的院子里总竖着箭靶。小时候父亲教他,“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少一样都不算真本事”。他读《孙子兵法》时,父亲就在旁边教他拉弓,说“纸上谈兵不如挽弓如月”。后来考中进士,成了文官,可每天晨起练箭的习惯从没断过,箭囊里的雕翎箭,磨得比笔杆还光滑。 辽主终于放下酒杯,干咳了两声。他盯着靶心那支颤动的箭,忽然问:“南朝文官,都有这般身手?”张叔夜躬身行礼,声音不高不低:“我大宋人才辈出,文者能谋国,武者能卫疆,臣不过是其中一分子。”这话不软不硬,既没吹嘘,也没自谦。辽主身边的大臣想反驳,可瞅着那稳稳当当的箭靶,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当晚的宴席气氛变了。辽人敬酒时,眼神里多了几分敬重。有个辽将端着酒走到张叔夜面前,竖起大拇指:“张大人这箭法,比我们草原上的射雕手不差!”张叔夜接过酒盏,和他碰了一下:“将军过奖,沙场之上,箭术是为保家卫国,不是为了宴饮助兴。”那辽将愣了愣,随即大笑:“说得好!敬保家卫国!” 这事很快传回宋朝。有人说张叔夜给大宋长了脸,也有人不解,一个文官练这么好的箭术做什么。张叔夜听到这些议论,只是照旧每天练箭、批阅文书。他心里清楚,辽国的轻视不是一天两天,光靠一支箭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让他们知道,大宋不是没人,更不是没骨气。 后来金兵南下,汴京告急。当时张叔夜已年近六旬,主动请缨带兵勤王。出发前,他把家里的弓擦拭干净,箭囊装满箭矢,就像当年在辽国宴射场上那样。敌军兵临城下时,他身先士卒,带着儿子们登城作战,箭无虚发。城破后被俘,金人劝他投降,他瞪着眼睛骂:“我张家世代忠良,岂肯做卖国贼!”最终绝食而亡。 史书里记张叔夜,多写他抗金的壮举,少提当年辽国那支箭。可那支箭的意义,其实和他后来守城时射出的箭一样——射的是敌人的轻视,护的是家国的尊严。文弱的外表下,藏着的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硬气,不管是提笔写策论,还是挽弓射强敌,只要国家需要,总能站出来,撑住一片天。 参考《宋史·张叔夜传》《三朝北盟会编》等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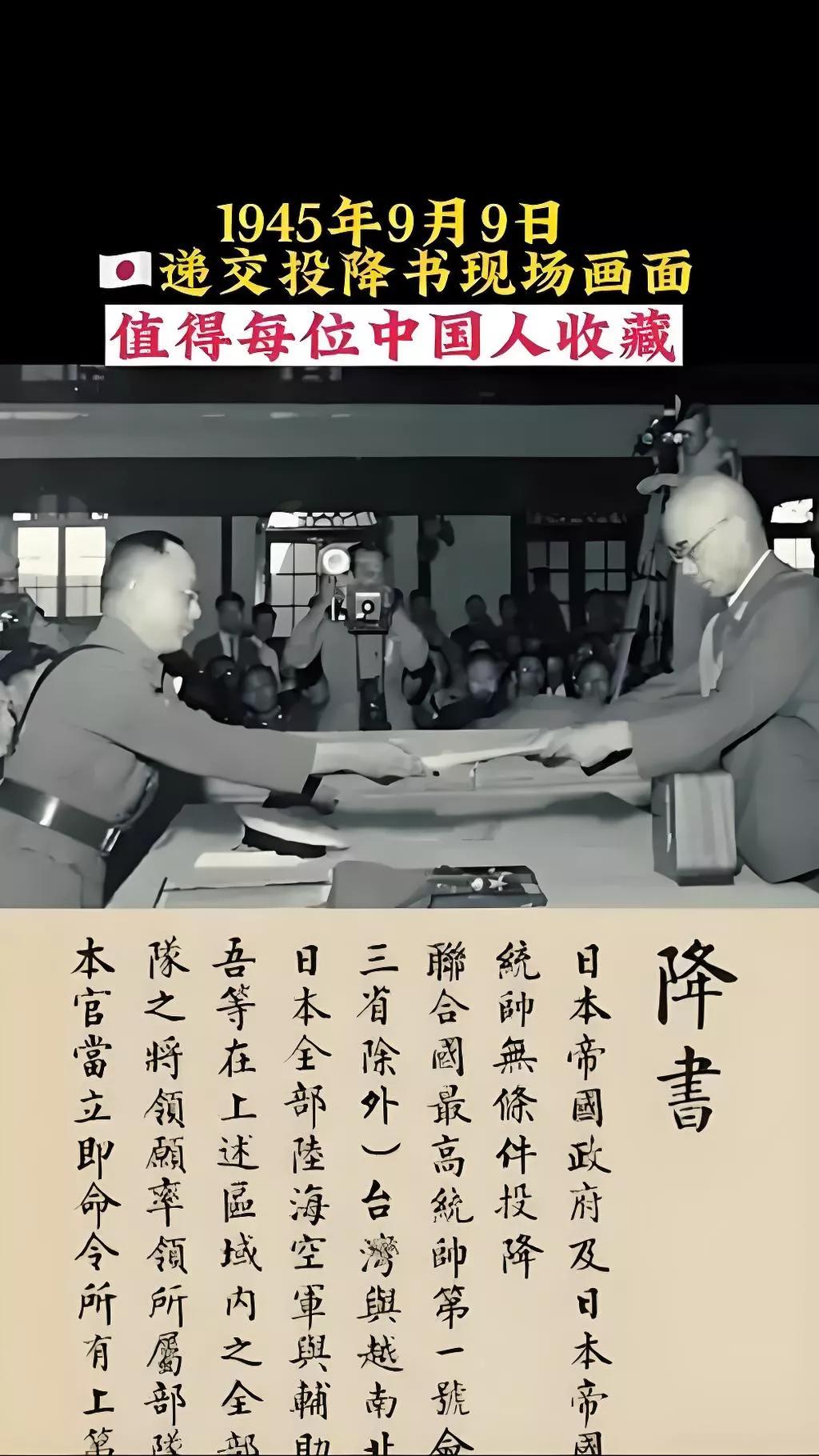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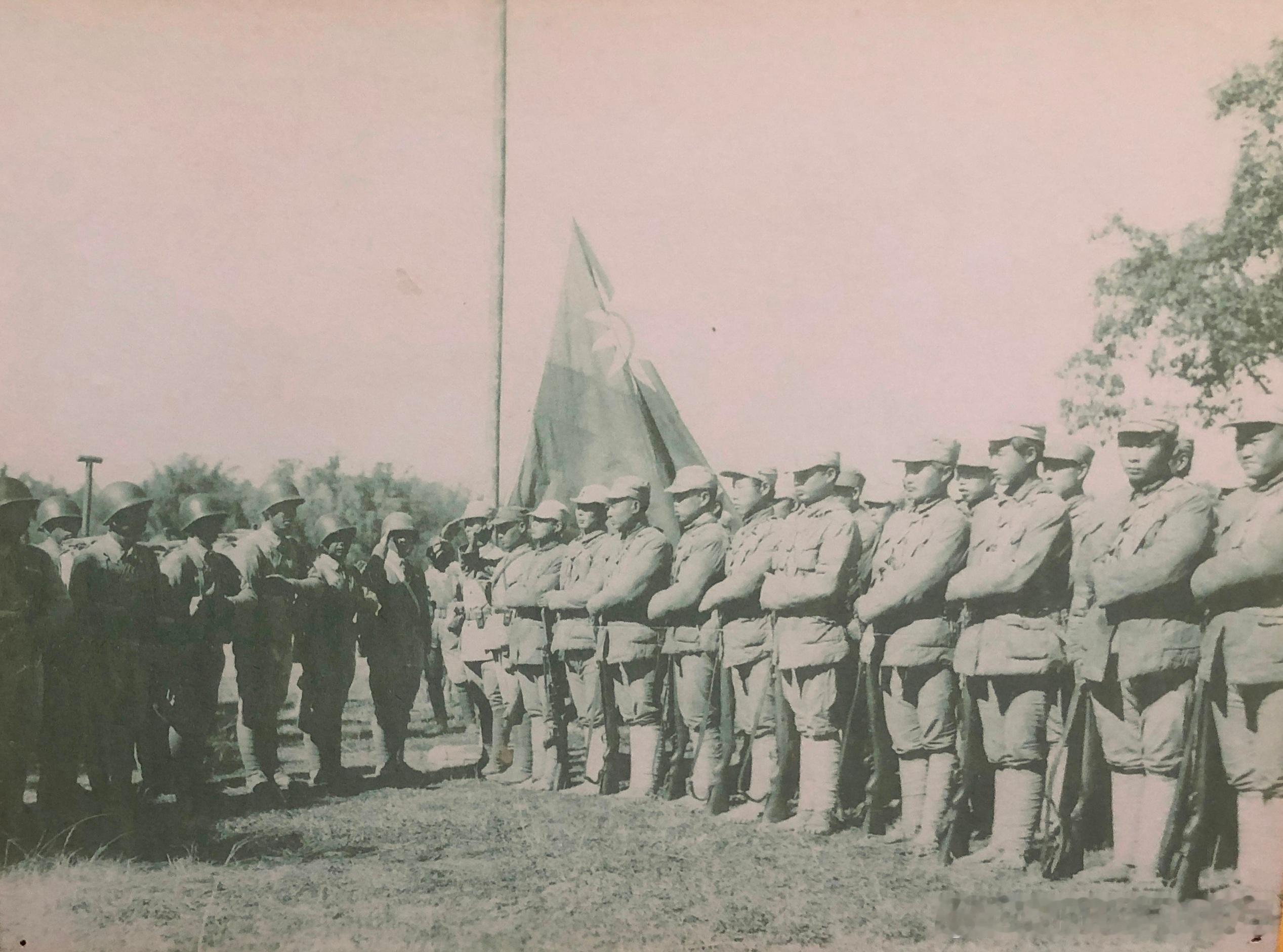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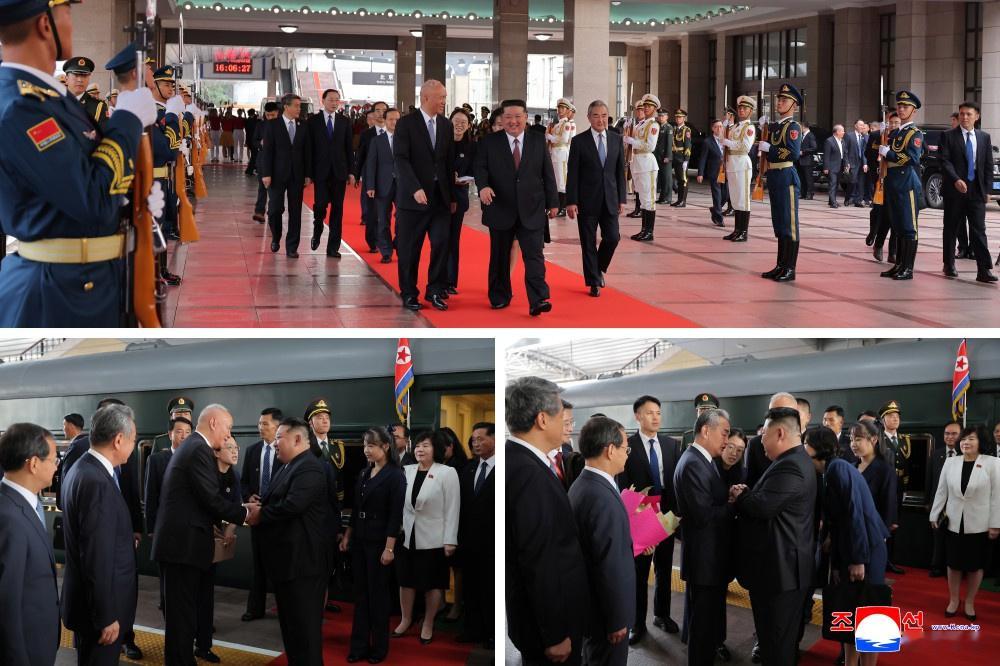




幺魚哥
还不是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