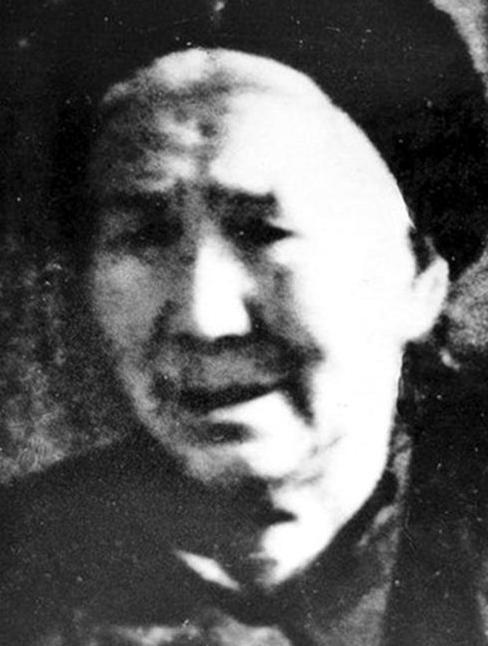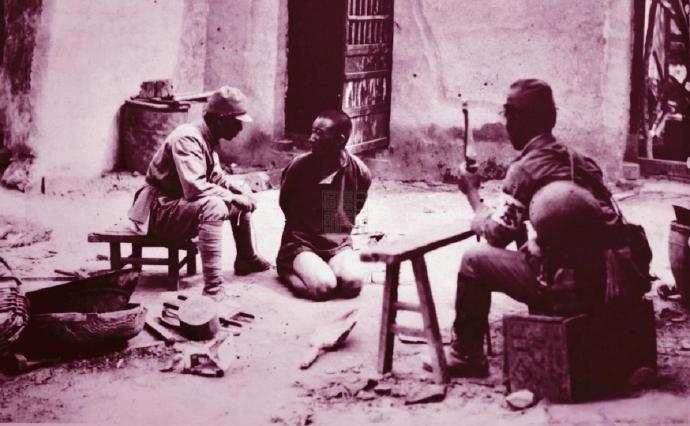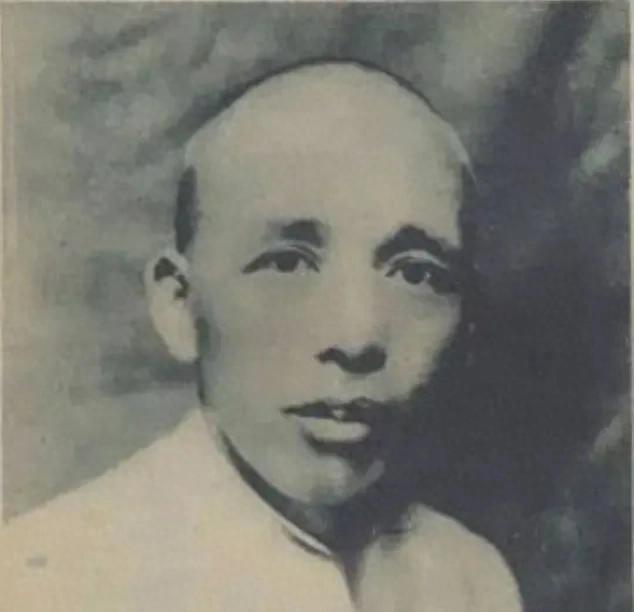1949年,58岁的邓玉芬喜极而泣,她原本以为七个儿子都已死,没想到老三永兴竟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了! 【消息源自:北京市密云区档案馆《丰滦密抗日斗争史料汇编》(1987年版)、邓玉芬长孙任连国2012年北京日报专访记录】 山里的雪还没化尽,邓玉芬蹲在灶台前吹火,柴禾湿得直冒青烟。她抹了把脸,指缝里都是黑灰。"娘,给。"七岁的小儿子递来半块窝头,孩子的手冻得通红。"你吃,娘不饿。"她把窝头掰成两半,大的那块塞回孩子手里。这是1940年的春天,猪头岭上的窝棚里,任家七口人已经吃了三个月的野菜汤。 山下的枪声突然密起来。邓玉芬扒着树杈往下看,十几个穿灰军装的人正往山上撤,最后头那个小战士腿瘸了,血滴在雪地上像撒了串红珠子。"是八路军!"大儿子永全抄起柴刀就要往下冲,被他爹任宗武一把拽住:"不要命了?鬼子就在后头追!"邓玉芬已经解开棉袄襟子,撕下里衬的白布条。 那天晚上,窝棚里多了个发高烧的小战士。邓玉芬用雪给他搓脚,孩子迷迷糊糊喊娘。"造孽啊,看着还没永全大呢。"她扭头对丈夫说,"咱家地没了,可人还在。人家拼命打鬼子,总得帮衬着。"任宗武闷头抽旱烟,烟锅子里的火星明明灭灭。三天后,夫妻俩送走了伤愈的战士,也送走了自家三个儿子。永全参军前跪着磕头:"娘,等打完鬼子,我给您挣个金镯子。"邓玉芬笑着拍他后脑勺:"傻小子,娘要镯子干啥?要你们全须全尾地回来。" 山坳里开始热闹起来。邓玉芬的窝棚成了"抗属接待站",今天藏个被烧了屋的寡妇,明天躲个寻夫的小媳妇。她总说:"添双筷子的事。"可自家粮缸早就见了底。1941年谷雨那天,任宗武带着两个儿子下山春耕,晌午没到,山道上就传来消息:鬼子扫荡,父子三人被堵在地里。邓玉芬疯了一样往山下跑,在村口老槐树下看见三具尸首——丈夫的手还攥着把稻种,五儿子永安的棉袄口袋里,躺着只没编完的蝈蝈笼。 "四哥呢?"小儿子扯她衣角问。邓玉芬这才发现,老四永合没在尸首堆里。半个月后,有人在据点外的乱葬岗认出了永合——这孩子被抓去修炮楼,逃跑时让鬼子用铁丝穿了锁骨吊死的。邓玉芬没哭,她把剩下的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记住,任家的男人,宁可站着死......"话没说完,十二岁的永恩就举起柴刀:"娘,我替爹和哥报仇!" 最难的抉择在1944年冬天。鬼子搜山,邓玉芬抱着小儿子藏进山洞。怀里的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洞外鬼子的皮靴声越来越近。"娘,我难受..."孩子刚要哭出声,她猛地抓起棉絮堵住孩子的嘴。等搜山的鬼子走远,怀里的身子已经凉了。后来村里人说,那晚听见山洞里有狼嚎,一声接一声,嚎到天亮。 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邓玉芬正在纳鞋底。线绳突然断了,针尖扎进指头,血珠冒出来,她盯着看了好久。活下来的三儿子永兴复员回家,刚进门就挨了记耳光:"逃兵!你兄弟们都..."话没说完,她自己先愣住了——永兴的左手只剩半个手掌。儿子轻声说:"辽沈战役丢的,没给您丢人。" 1970年冬天,79岁的邓玉芬在扫雪时摔了一跤。临终前她盯着房梁,突然说了句:"老五该娶媳妇了。"守灵的乡亲们发现,老人枕头底下压着七双布鞋,鞋底纳得密密实实,像是要给远行的人准备。如今在密云烈士陵园,她的墓碑旁栽着七棵柏树,最高的那棵已经超过三层楼——那是长子永全参军那年栽的,树底下埋着那只没送出去的金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