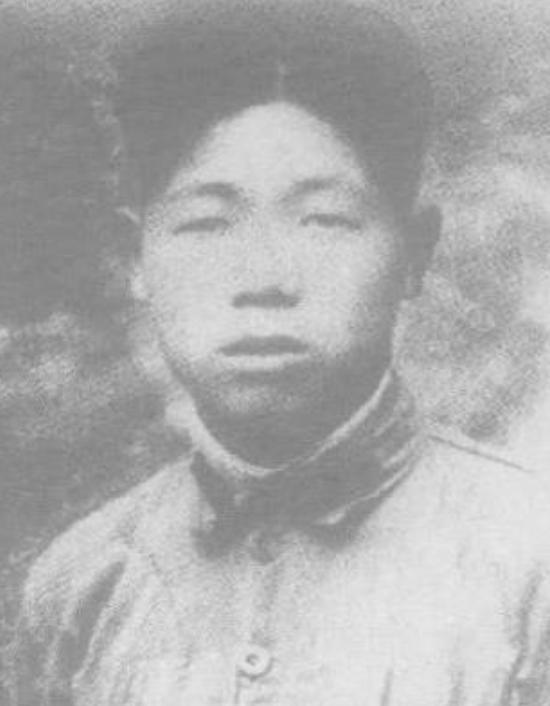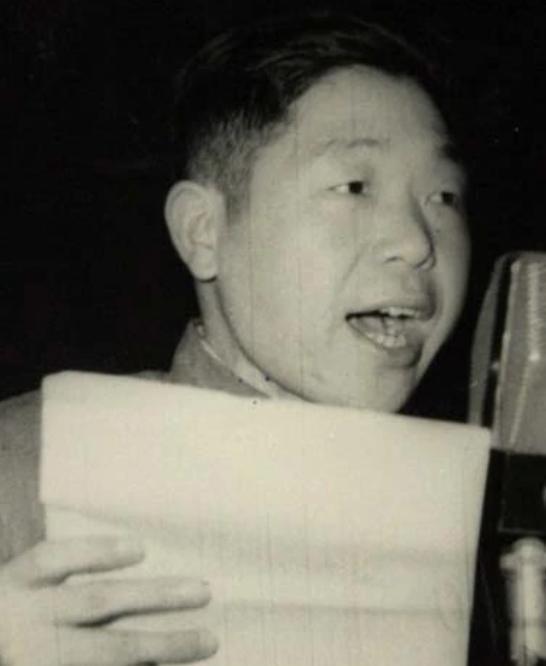陈锡联家中,毛主席像挂了26年,他叮嘱家人:谁也别想把它摘下来 【1990年初冬】“爸,客厅墙漆得这么新,毛主席像是不是先取下来?”刚刷完墙的儿子抬头问。陈锡联坐在藤椅里,抿了口热茶,语气不高却很硬:“想都别想,除非哪天我不在了。”短短一句,把全家人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一幅半身像,自1973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后就挂在墙上。二十几载,墙面换过颜色,挂钩也修过好几回,画像却分毫未动。老将军年纪越大,神情越柔和,可谈到这幅像,态度始终如钢——它既是领袖的目光,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坐标。 亲友不止一次好奇:前线出生入死的人不少,能与毛主席相处的也不少,为何陈锡联特别执着?他从不长篇大论,只笑着摆手:“我这条命,是共产党给的,是毛主席给的。”听上去像客套,实际上是他喊了一辈子的心声。 将时间拨回到1915年正月,湖北黄安高桥的冬晨冷得像刀子。刚出生的陈锡联还没长大,父亲就病逝了。饿过太多肚子,他八岁就去地主家放牛。那年秋天,他不小心打碎了猫碗被扣了晚饭,哭着跑回家,一头扎进母亲怀里。母亲的棉衣破得露棉花,依旧用粗糙的手抚着他,那样的温度,比炕火还暖,也把一个孩子的倔劲儿彻底点燃。 十岁那年,他编草垫子逮鱼给母亲加餐,第一次尝到“用脑子”胜过“用蛮力”的滋味。也正是那几年,黄麻起义的枪声震动乡村。徐海东的游击队在附近打得热闹,陈锡联越听越热血。母亲担心他没命,他却趁夜爬窗,跑去报了名。从此,放牛娃变成红军小号手。 初上战场,他什么都不懂,只记得一个念头:绝不能再让地主骑在穷人头上。1931年,部队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他当上通讯连指导员。一次夜袭,他带三名战士悄悄翻到山顶,先端了敌连部,天还没亮就俘虏百余人,全连无伤。李先念拍拍他肩膀笑说:“小钢炮,打仗你数第一。”这外号从此跟着他上南下北。 抗战爆发,陈锡联任八路军769团团长。1937年10月夜袭阳明堡机场,24架敌机被毁。卫立煌专电称赞,那是中国陆军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果。有人问他策划细节,他只提一句:“老百姓的线索最金贵。”那场胜利后,他第一次在太行山区远远见到毛主席视察部队。隔着人群,领袖扬手致意,年轻的团长立正敬礼,眼眶却红了——他想起小时候挨饿时对自己说过的那句“总要有一天,不再看地主脸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陈锡联先在重庆兼任市委负责人。刚到任,他走上街头,看见成群结队的流浪汉。城市满目疮痍,战火留下的是空洞的眼神。他把这些人集中到收容所,给热水、给棉衣,再送到成渝铁路工地挣钱。一个工人边流泪边跪下叫他“陈青天”,他忙不迭扶起:“别谢我,谢共产党,谢毛主席。”这句话后来传遍码头,也传进北京。 1950年春,毛主席在香山召见陈锡联,话音一贯风趣:“红四方面军那个小钢炮,还记得不?让他去搞真炮!”就这样,他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那几年,国内百废待兴,工业底子薄,导轨、测距仪、弹道计算全靠摸索。陈锡联带着技术人员一天跑三个厂,能用的全拆下来,不够的就画图纸重造。有人劝他悠着点,他摇头:“炮弹飞出去,伤的是战士,慢不得。” 朝鲜战场上,上甘岭炮火声震得山体都在颤。他坐在指挥所里,连着七天七夜没合眼,嗓子喊哑,额头撞在钢盔上出了血也没发现。最终志愿军顶住了“联合国军”900多次冲锋,炮兵功不可没。作战结束,毛主席特意夸奖:“炮火准,打得好。”陈锡联轻声回答:“主席放心,咱们的炮兵再远也打得到。”说罢,他咳嗽了好久,谁也不知道那一口血是在什么时候咽回去的。 进入70年代,他身体大不如前,但处理起部队事务依旧干净利落。1976年9月,噩耗传来,举国悲恸。陈锡联回家,把毛主席像擦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还是抬手敬了个军礼。饶是铁骨,也有泪水悄悄滴在军帽檐上。 画像就这样挂在会客厅里,春去秋来,从不改位置。外孙女小学作文里写:“外公说墙会老,像不会老。”老师批注:这孩子的家教不一般。其实谁知道,老将军自己有时坐在画像下,摸着那把陪了他多年的军刀,眼神远得像在回太行山听号角。 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走完他传奇的一生,享年八十四岁。治丧小组布置灵堂时,家人问是否把那幅像移到祭堂正中,老人的秘书翻出遗嘱,只一句:“原位不动。”最终,画像仍在老地方,默默注视着匆匆来往的吊唁者,就像以前注视他策马冲锋,也注视他伏案批阅。 二十六年,一幅画像,一位将军。客厅并不大,却承载了他对领袖、对信仰、对战友和对这片土地的全部情义。很多来悼念的老兵看着那张熟悉的笑容,会有意识地立正,然后敬礼——动作和当年在延安窑洞前一模一样,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也有人问,这样的坚持值不值得?答案或许只有陈锡联自己最清楚:当年牛背上的放羊娃,看见“穷人当家作主”的火种,才有了后来炮火中冲锋的虎将。画像留在墙上,不只是纪念个人的缘分,更提醒后来者——路没走到头,劲儿就不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