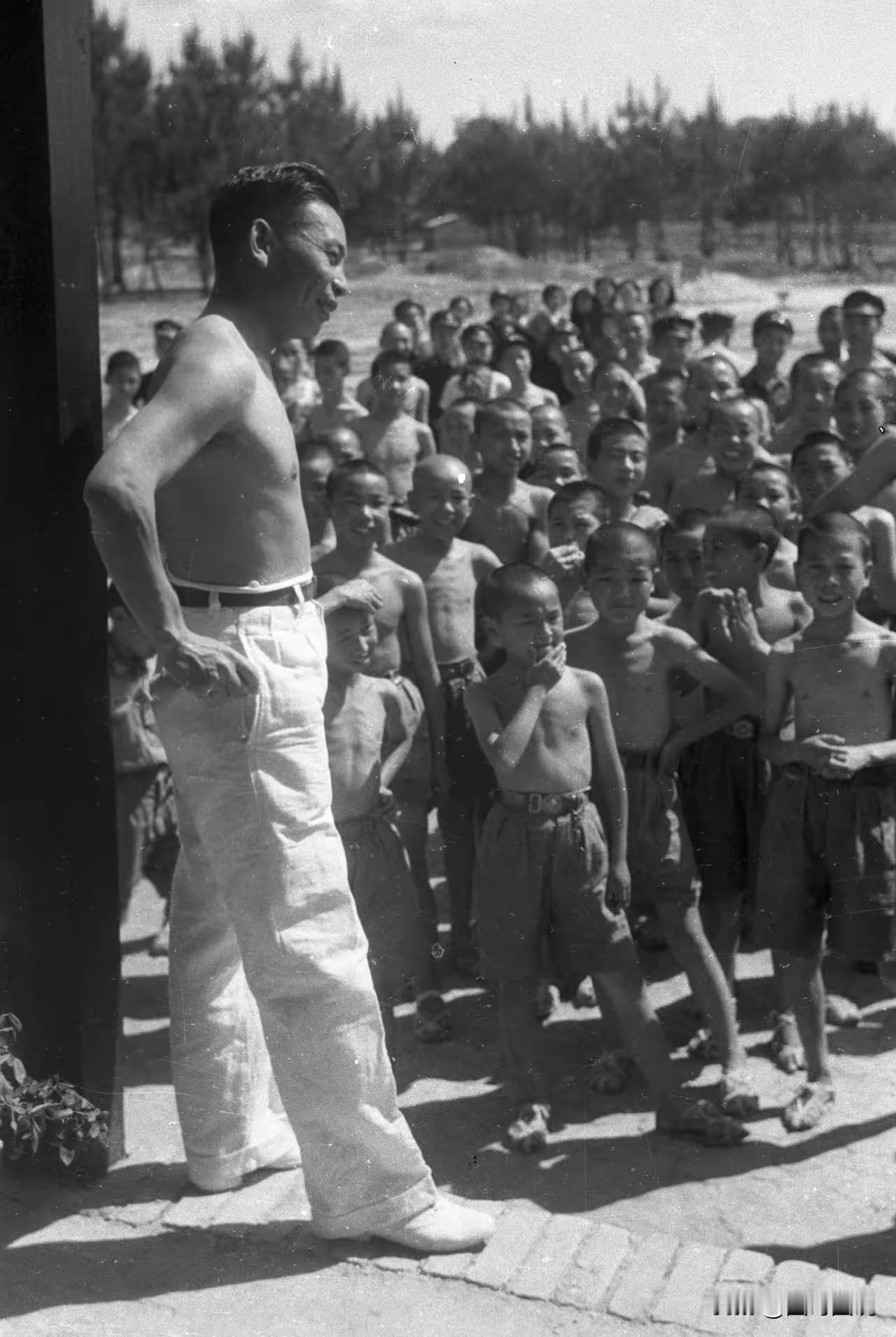1967年,马思聪叛逃香港的消息让无数人感到震惊,当时的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如此声名显赫的人物,为何要选择叛逃香港,甚至不惜背负叛徒这一千古骂名呢? 1967年1月15日深夜,珠江口55岁的马思聪把小提琴盒抱在怀里。 妻子王慕理,身边跟着19岁的女儿马瑞雪。 他们刚从广州郊区的小码头摸黑登船,目标是香港。 此刻没人敢想,这位被称为“中国小提琴之父”的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会以“叛逃者”的身份,开启漂泊异国的余生。 马思聪1912年出生在书香门第,打小就浸在民间音乐的养分里。 父亲的藏书里有戏文,连保姆哄他睡觉都哼着本土小调。 这些“土得掉渣”的旋律,后来成了他音乐里最鲜活的魂。 11岁那年,大哥把他带到法国。 南锡音乐学院的琴房里,他练到手指流血。 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名师跟前,他把小提琴技巧磨得锃亮。 17岁回国时,他已经能拉出帕格尼尼的协奏曲,上海媒体直接喊他“中国音乐神童”。 抗战爆发后,他背着小提琴跑遍华南西南。 在桂林的防空洞前,在昆明的街头,他拉着《思乡曲》。 解放后,他留在大陆,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 他教出刘诗昆、林耀基这样的弟子,把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民歌揉在一起写组曲,还率团去捷克参加音乐节、当肖邦比赛评委。 那时的马思聪,是“中国音乐的名片”,连《思乡曲》都成了广播对台的开场曲,传遍海峡两岸。 1966年夏天,北京的风突然变冷。 作为学院院长,马思聪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8月9日,他被带进隔离室,每天写不完的材料,出门要报告,墙上贴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标语。 更疼的是《思乡曲》被禁。 11月28日,广播里突然没了这首陪伴他几十年的曲子。 对一个音乐家来说,这等于割断了创作的根。 紧接着,肝病发作,他被允许回家,但监视没松。 楼道里总有陌生人晃悠,邻居的眼神也让他刺挠。 家人先撑不住了。 8月14日,王慕理带着孩子南下,从北京到南京再到广州,投奔亲戚。 马思聪则在11月22日,跟着女儿马瑞雪坐火车追上去。 一家人在广州江门的农舍里聚齐,挤在小屋里偷偷商量:“再这样下去,连命都保不住。” 1967年1月,广州的巡查越来越严。 马思聪知道,必须走了。 1月15日晚,他们换了普通衣服,步行到珠江口码头,登上黄埔002号拖船的木驳子。 船里挤了13个人,风浪里马思聪紧紧抱着琴盒。 凌晨到香港新界浅滩,一家人涉水上岸,步行一公里到安全点,只敢喘口气,第二天就飞纽约。 这一路,他想的不是“叛逃”,是“活下来继续拉琴”。 出走前,他被批斗时剪了头发,挂牌游街,尊严早没了。 他的曲子被禁,创作的路断了,连家人的安全都没法保证。 后来他在美国说:“我不是叛徒,我只是想保住自己的艺术生命。” 到美国后,马思聪住在费城的小公寓里。 他拒领政治救济,靠子女的工资过日子,每天拉琴、作曲。 他写了20多首中国主题的作品,比如《牧歌变奏曲》。 偶尔去社区演出,拉《思乡曲》时,台下的华人会哭。 他们听懂了,这不是曲子,是一个老人藏在琴弦里的乡愁。 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叛徒”。 晚年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爱音乐。我只是不想被毁了艺术,不想连累家人。” 1984年底,公安部决定平反马思聪的冤案。 1985年2月,文化部的公函送到他手里,此时他已经在病床上,胸闷得厉害。 他想回国看看,可身体不允许。 1987年5月,马思聪在费城做了心脏手术。 20天后,他走了,75岁。 2007年,儿子马如龙把父母的骨灰护送回广州。 马思聪的一生,像一把被揉皱的小提琴。 他带着“叛徒”的骂名出走,却从未放下对祖国的爱。 他在异国拉了一辈子琴,琴声里全是乡愁。 如今,当我们再听《思乡曲》,或许该懂那不是一个“叛逃者”的怨恨,是一个艺术家对纯粹的坚守,是一个老人藏在琴弦里的,未说出口的“我想回家”。 历史会记住他的贡献,也会原谅他的无奈。 毕竟,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最痛的不是骂名,是再也拉不了祖国的曲子。 主要信源:(南方新闻网——广汕记|小提琴家马思聪的广州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