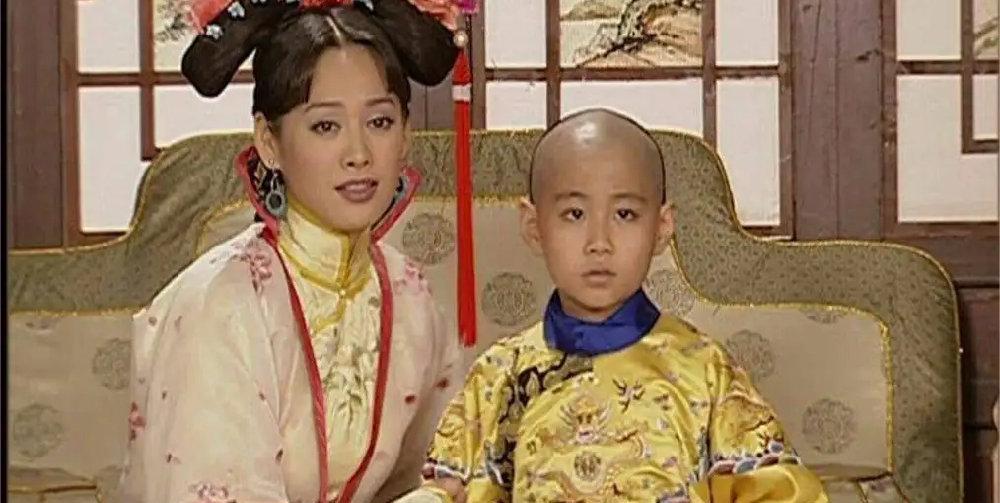北魏权臣高澄郊游,遇到了一个漂亮尼姑,就强行连夜逼她一起谈佛法,然后带回宫中,生了个孩子,就是世间第一美男子高长恭。 那尼姑法号叫什么,史书里没细说,只说她原是五台山附近庵堂里的修行者,生得眉目清婉,寻常荆钗布裙也掩不住一身温润气。高澄那日带着随从在郊外射猎,歇脚时见她在山溪边浣洗衣物,阳光落在她素白的僧袍上,竟看得有些发怔。他那时正是权倾朝野的年纪,性子骄纵,见了合心意的,从没有“商量”二字。 随从们把人架走时,她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僧衣,指尖被溪水泡得发白。夜里被安置在临时搭建的营帐里,高澄倒真搬了些佛经来,却半句没提“色即是空”,只盯着她的脸笑:“你这般模样,青灯古佛前坐着,倒是委屈了。”她垂着眼,睫毛颤得像风中的蝶,始终没说一句话。 带回宫后,她被安置在偏殿,没给任何名分。宫人们见她穿着半旧的僧袍,总爱私下议论,说她是“被强掳来的野尼”。她从不辩解,每日晨起仍会对着窗棂静坐片刻,手里捻着的念珠磨得光滑,像是带了许多年。 高长恭出生那天,宫里落了场细雪。接生的稳婆抱着襁褓出来,只说这孩子生得“粉雕玉琢,从没见过这般齐整的娃娃”。高澄来看了一眼,见孩子眉眼像极了那尼姑,尤其是眼尾那点浅浅的弧度,忽然叹了句:“留下吧。” 那尼姑教他认字,教他背《金刚经》,却从不说自己的过去,也不提高澄。有回高长恭指着画像上的高澄问:“那是谁?”她愣了愣,才轻声道:“是能护着你的人。”话虽如此,她却总在夜里对着月光发呆,指尖一遍遍划过念珠。 高长恭十岁那年,出落得越发俊朗,走在宫里,连扫地的老太监都要多看两眼。可这份美貌没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反而招了不少闲话。皇子们聚在一块儿玩,总有人笑他“没娘的野种”,把他的弓箭扔到泥里。他从不跟人争执,捡起来擦干净,第二天接着练,箭术反倒比谁都好。 十三岁上,高澄遇刺身亡,宫里乱了一阵。有人说该把这“来路不明”的孩子赶出宫,是他母亲第一次在人前跪了下来,对着新掌权的高洋(高澄之弟)磕了三个头:“他是高家的骨血,求陛下让他自食其力。”高洋看着这对母子,想起小时候见过这尼姑安静诵经的样子,竟点了头。 从此高长恭开始在军中历练。他怕自己的容貌让人轻视,每次上战场都戴一副狰狞的铁面具。第一次领兵打仗,对手见他年纪轻,又是出了名的“美公子”,压根没放在心上。谁知他一马当先,面具下的眼神冷得像冰,手中长槊舞得风雨不透,硬生生撕开了敌军的防线。 战后清点俘虏,有个老卒颤巍巍地说:“将军摘下面具时,我还以为是菩萨降世,可那枪法,比阎罗还狠。”这话传到高长恭耳朵里,他只是笑了笑,把赏下来的绸缎全分给了伤兵。 他母亲那时已搬出皇宫,在城郊结了个小庵堂,依旧青灯古佛。高长恭每次出征前,必去看她,母子俩对着坐半晌,不说什么话。有回她摸着儿子脸上的疤痕(练箭时被划伤的),轻声道:“容貌是天生的,可行事端正,才是立身之本。”高长恭点头,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后来他成了北齐的“兰陵王”,战功赫赫,却从不居功。手下的兵说,将军最见不得百姓受苦,路过灾区,会把自己的干粮分给流民。宫里的人说,兰陵王从不参与党争,别人送礼他全退回去,只爱跟军中的弟兄们在一块儿。 有人问他,会不会怨当年父亲的做法,让母亲受了委屈。他望着远处的太行山,那里有母亲修行的庵堂,轻声道:“过去的事,算不清了。我能做的,是让母亲如今能安稳念经,让跟着我的弟兄们能平安回家。” 他的故事后来越传越远,人们记着他的美貌,更记着他的勇猛与仁厚。连敌国的士兵都知道,北齐有个戴面具的将军,打仗厉害,心却善得很。 据《北齐书·兰陵武王孝瓘传》记载